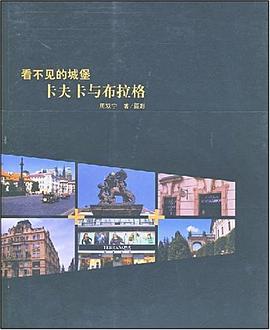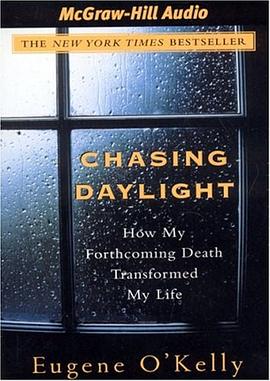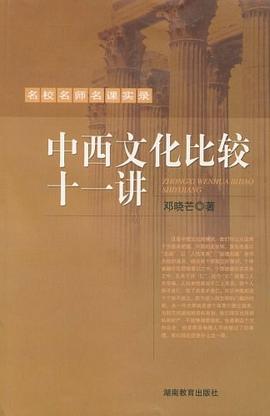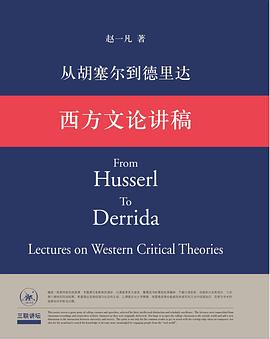具体描述
一场穿越时空惊、险离奇的植物考古学之旅。书中,作者与大家一起分享人类最古老的农业园艺活动,了解人类祖先为原始植物命名的曲折历程,介绍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植物及其习性和分类,也告诉我们,人类祖先是如何敬畏大自然、信仰大自然对物种的安排。图文并茂,为爱好大自然的读者带来惊喜。
作者简介
安娜·帕福德,英国《独立报》园艺版记者,《观察家》、《乡村生活》和《Elle装潢》等多家杂志的专栏作家,曾写作《郁金香》、《花坛全书》、《植物拍档》等八部作品,其中《郁金香》最为畅销。她是英国古迹保护组织成员、古代园林及建筑修缮工作的负责人,曾耗时近三十年参与重新修复了原属该地区首席神父的花园。近年来,她又开始了另一处花园的修葺。
目录信息
第一章 开篇
第二章 生而知之,学而知之
第三章 亚历山大图书馆
第四章 剽窃者普林尼
第五章 求药之人
第六章 女王宝典
第七章 阿拉伯人对植物学的影响
第八章 黑洞效应
第九章 准人妙手绘丹青
第十章 复活的狄奥弗拉斯图
第十一章 布伦费尔斯的著作
第十二章 一介狂狷写性灵
第十三章 意大利之旅
第十四章 第一座植物园的诞生
第十五章 长鼻子的挑剔者
第十六章 威廉·特纳结下的网
第十七章 新教盛世
第十八章 格斯纳的著作
第十九章 新牧场
第二十章 普朗坦的队伍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草药书
第二十二章 英国人的成就
第二十三章 连线美洲
第二十四章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尾声
名人志
序言
我还记得骑马与哈萨克牧马人一起穿越中亚天山山脉的情形。当时是四月末,一场暴风雪刚刚席卷了白雪皑皑的连绵山脉,阳光重新照耀大地,一道彩虹横跨在广阔而又平坦的平原上。平原上有许多苏维埃时期废弃的产业——破败不堪的灌溉渠,支离破碎的天然气管道,还有荒废的工厂。广阔的平原从北面的天山山脉脚下,一直延伸到下一个山脉(卡拉套山)的起点处。卡拉套山巍然耸立,直插云霄。水汽从我前面的灰点马狭窄的腰窝两侧,以及放在马背上的粗糙的帆布鞍囊上不断升腾。我的马鞍配有一块鲜艳光滑的天鹅绒坐垫,固定在一个船形的金属框架上,缰绳是编织而成的,马头两侧的颊革上绑着一些红色的碎布条。在穿越村庄和丘陵地带绿草茵茵、广阔平坦的平原时,这些马匹健步如飞,非常轻快。在跳跃草场上狭窄的溪流时,它们会做出酷似摇马玩具一样奇怪的跳跃动作。现在,道路情况变得崎岖不平,险境环生,我根本看不到一丁点车辙的痕迹,只能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马匹的行走路线。它们在四季常青的刺柏属植物生长的土墩间跃进跃出,在巨石的边缘擦身而过,滑下泥泞不堪的河岸以穿越因雨水而变得高涨的河流。有时候,我们的马也会打乱那些红腿石鸡的宁静生活,后者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锡玩具一样从刺柏丛中扑棱棱地蹿出来。
水滴从哈萨克牧马人的帽子边缘滴下,这种帽子的材料就像渔民所穿的油布长雨衣,帽子的前端弯曲向上,其中一边一路向下到达背部的脖子部位。它是由厚厚的毡制品制成,我们在山顶斜坡上看到的那些牧羊人的圆顶帐篷也是由这种材料制成的。绕过一处断崖,我们的眼前豁然出现了一片高原。在这里,有红褐色的贝母属植物、蓝鸢尾、藏红花,长有成片的蛇皮那样杂色叶子的郁金香,还有粉红色的观赏性樱桃,葱属植物,成片的紫罗兰、大茴香、紫堇属植物,垂吊状的名为“所罗门的封印”的花,叶子呈箭头状的黑海芋满山遍野,密密麻麻,简直比哈萨克人地毯上的针脚还要细密。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植物,而且能够说出它们各自的名字,是因为在西方国家,植物爱好者们通常会自己尝试种植这些植物,尝试说服它们告别天山山脉叶岩密布的斜坡,告别夏日里热得足以超出体温计承受极限的高温,以适应新地方的潮湿黏土,当然还有夏日里那阴云密布、细雨霏霏的生存环境。这些植物都是植物王国中色彩艳丽无法抗拒的超级明星。自从人类第一次看到它们之后,它们就注定要拥有一个比大自然为它们挑选的位于中亚一角的这个生存环境更加广阔的生存舞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随着欧洲大使进驻新的土耳其帝国首都,东方植物也由此被引入了欧洲,而且数量非常庞大。在15世纪中期到16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由东方引入欧洲的植物数量几乎相当于过去两千年中引入数量总和的20倍。沿着昔日的丝绸之路——这条历史悠久的通商路线,东方的商品制造者将大量价值不菲的货物销给西芳的顾客。
当我的马挑剔地咀嚼着顶冰花和野玫瑰之间夹杂的嫩草时,我却在为其他事情忙个不停——那些行李托运车、鞍囊、手工制作的马具必须检查妥当,免得早晨出发时手忙脚乱。夜幕降临前,圆顶帐篷要马上搭好,还要赶紧架起熊熊火堆,吓退随时可能出现的熊或狼群。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些装置和设备,要想将植物从它们的自然栖息地原封不动地带走,就全靠它们了。这些植物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转运途中幸存下来,因为它们最重要的部分是鳞茎。一旦已经开花,植物就会通过鳞茎在夏季快速地摄取各种营养,然后在地下休养生息,覆盖在鳞茎上面的坚硬土壤有效地遮蔽了阳光。因此在蛰伏的这几个月里,鳞茎就算被携带到遥远的地区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密封完好的它们可以暂停生长。正如赋予这条古代通商路线名字的丝一样,鳞茎体积小,价值高,因此商人们为得到它们不惜冒很大的风险。
牧马人亚历山大刚刚一直在采集蘑菇和青紫色的食用伞菌,后者的凸出部分就像花丛中挺立的奶油色石头一样。突然,他指着一丛野生龙蒿旁的一堆新鲜粪便大叫:“附近有熊!”这头熊早餐吃的是杜松子,午餐享用的则是大黄。亚历山大认为这头熊肯定是在我们头顶的洞穴里过冬。洞穴外生长着一大片贝母,现在已经全部绽放。这种花在欧洲的园丁看来,应该是这一科中最罕见、最奇特,也是最难种植的一个种类,现在却成了“熊舍”前普普通通的花园装饰。这些贝母和荨麻一样长得密密麻麻,茎干上伸展出带有螺纹和白霜的叶子,叶子表面装饰有许多奇怪且令人心动的黄色钟形图案。
我的马穿过一大片黄色鸢尾地前去和亚历山大的马会合,马蹄下许多花被踩得乱七八糟。看着它们带有白边的宽阔叶子被踩得粉碎,我忍不住对它们表示抱歉。我以前在皇家植物园只见过一次这种花,它就长在一个黏土制成的器皿中,只有孤零零的一朵花,这是由英国唯一一位能够培育它开花的人种植的。“鸢尾!”我对亚历山大说道,亚历山大则马上用他那掺杂了一点儿俄语口音的哈萨克语回应我说:“当地人管鸢尾叫做乌克拉。”“鸢尾美人蕉?!”我随口说出了它的通用名称,与其说是想告诉亚历山大,倒不如说是在提醒自己,因为这是它的植物名和别名,也是它在哈萨克以外地区的通行证,只要脖子上挂着这个标签,它的“特殊身份”便无人不晓了(哈萨克地区的鸢尾具有和其他在中亚生长的鸢尾截然不同的特征)。“鸢尾美人蕉”这个名字是由法国分类学家埃利一阿贝尔‘卡里埃在1880年为其命名的(他曾经在一位园丁的收藏中见过这种植物,随后在《园艺学评论》中第一次对其进行了介绍)。此后这个名字便在西班牙人、比利时人、美国人、澳大利亚人、巴西人,甚至日本人等各色人种之间传递。自西欧中世纪时期以前,作为欧洲主要的书面语之一的拉丁语,起初一直和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及荷兰语平分秋色,然而自第一本草药书以拉丁语为植物命名时起,在随后的三百年里,这种模式日臻完善,并逐渐形成一种特殊的植物学语言。对此,世界各地凡是对植物感兴趣的人都能够理解。然而,标签对植物本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数百万年来,植物只会对一些外部的刺激物,如光线、黑暗、温暖、寒冷、潮湿、干燥、马蹄的踩踏等等做出反应。亚历山大对此也不太感兴趣,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了扎尔巴克利——这座位于平原下面的小村子里,而且在我看来,他也极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度过余生。目前,亚历山大至少可以随口叫出这片山区80%的植物的通用名,而他所熟识的这些植物,各个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例如,当地人把梨称作“格鲁沙”,把荨麻称作“克拉皮瓦”,把郁金香称作“凯斯卡尔达克”。亚历山大采集的那些蘑菇,被当地人称作“西纳诺兹卡”,亚历山大在兜售这些蘑菇时也喜欢这么说,一来是为了向客人强调这些蘑菇是无毒的,二来作为一种美味佳肴,“西纳诺兹卡”早已名声广播,因此他能够以很高的价格将其卖给周边地区的人们。
但是,所有这些令人惊异的植物在它们到达远离家园的异国他乡之后,又是怎样得到另外一种全新的、琅琅上口的当地通用名的呢?这些纤弱的植物先是经由商人之手被送到船长手中,而后再从旅行者到园丁,从外交家到贵族,从使节到僧侣,经由各式各样人群的传递之后,它们从中亚故乡千里迢迢迁居至比萨、帕多瓦、普罗旺斯、巴黎、莱顿,乃至伦敦。此时此刻,它们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惯用名。虽然没有了老“户籍”,仅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人们也必须为这些远道而来的娇客们安排新的“身份”。许多植物在引入欧洲后都被当成药物使用,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增加药材商可用药物的范围,同时提升草药的效用。当时,绝大多数药物都是由草药(它们通常被称为药草)配制而成的,假设药物成分全都名副其实的话,这些新的药物成分有望提供新的治愈希望。一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取决于植物采集者区别不同植物种类的能力,它的经济价值则会随着药用价值的提升而水涨船高。
但是,一些药剂师担心草药经常会被那些更容易获得的植物鱼目混珠,而这正是托马斯·约翰逊和他的朋友们前往肯特郡采集植物的主要原因。托马斯等人计划前往英国不同地区采集植物,收集他们看到的各种野生植物标本,描述它们的主要特征和已知用途。这次探寻只不过是一系列探险行动的开始,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尝试,药剂师们第一次将在英国生长的植物与它们应有的名称进行对号入座。
事实上,早在英国之前,给植物命名的工作就已经在意大利和法国展开。约翰逊开始这段旅程的想法和动机也是受了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的影响,他的事迹令约翰逊大为鼓舞——这位年轻的意大利植物学家曾在1557年前往西比林山脉进行探险活动,这也是整个欧洲地区第一次旨在记录特定地区及当地植物群落的探险行动。当然,那时候的乌利塞并没有称自己是植物学家,植物学家这个名词是在这次探险行动结束一百多年之后才在出版物上出现的。植物研究与医学研究自始至终都紧密联系在一起。16世纪的药剂师、外科医生或内科医生,各个都是植物栽种的高手,要想精通医理,就必须对各种草药的药性驾轻就熟。阿尔德罗万迪也曾专程到意大利城市博洛尼亚,向伟大的植物学家卢卡·吉尼虚心求教。因此,早在16世纪,植物学就已经成为泛欧陆地区知识与物资传播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神秘的领域不仅仅是一个吞吐大量信息的交换平台,更是一道无形的网络,把那些希望对自然世界有更多了解的人网罗到一起。然而随着认知的不断深入,为了使庞杂的自然万物有序化,就必须建立一套命名体系。自然界的动植物除原有的拉丁名称外,还必须有一个常用名,这个常用名不仅要获得本国大多数研究者的一致同意,而且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与理解。为此,刚刚三十出头的阿尔德罗万迪和西班牙极具影响力的药剂师博加索建立了联系。同时他还与腓力二世时期驻马德里的教皇特使毕晓普·罗萨诺、巴塞罗那医生米孔·德威兹互递信息,和法国马林斯的植物园园主菲利普·布朗雄交换种子。1578年,皇冠贝母刚刚从东方传到欧洲,阿尔德罗万迪便送给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这位在普拉特里诺拥有一座著名花园的大公——一张绘有皇冠贝母的油画。
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能够被组织得井井有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植物命名系统。命名学的发展又和欧洲的学者以及他们的赞助人,还有贵族以及土地所有者组成的网络系统紧密相连,所有这些人都是通过一种公共语言,也就是拉丁语进行交流的。当然,对自然认知的渴求只是部分原因,除此之外,药物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及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都是促使科学家们实现“将各种植物对号入座”的重要原因。人们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自然世界,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典型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的、非宗教的因素逐渐超越了中世纪欧洲长期形成的宗教冥想模式。新时期的精神文化极大推动了古典学识的复兴、科学发现、地理探险等活动,同时充分发挥了人类大脑的潜力。艺术也挣脱了宗教的束缚。随着一种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思维模式的成熟,有关自然世界的研究和分类工作成为了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和关键的组成部分。14世纪的人们在实验研究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比如严酷的冬天、食物匮乏、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等。作为15世纪上半叶的重要特征,实验研究标志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植物学家、草药医生、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往来于欧亚两个大陆的外交家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卓有成效的紧密关系。威尼斯大使安德烈亚·纳瓦格罗曾骑马在巴塞罗那和塞维利亚两地之间旅行,对当地阿拉伯农民种植的各种庄稼做了详尽的记录。贵族安东尼奥’米歇尔于1510年出生于威尼斯,他在威尼斯的特雷维索岛拥有一座漂亮的花园。米歇尔曾收到过驻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威尼斯大使送来的植物,他与达尔马提亚、克里特岛以及黎凡特等地区一直保持着联系,和那些与威尼斯有生意往来的法国、德国及佛兰德商人的关系也很密切。由于欧洲的许多贸易往来都要通过意大利的港口,也就难怪意大利在探索植物世界序列的过程中走在前列了。来自地中海地区的学者们将最新的资讯迅速地传向四面八方,这些信息甚至传递到偏远的北欧地区,于是威尼斯、佛罗伦萨、普罗旺斯、巴黎、莱顿和伦敦就被这样一条条无形的信息链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印刷术的发明对知识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1454年,在美因茨出版的由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发的《赎罪券》就是利用这种新工艺生产的第一套印刷品)。在此之前,信息只是一种个人资产或者财富,只能按照信息所有者的意愿,通过口头或者书信的方式进行传播,每个掌握信息的人在将它传递给其他人之前都可以添加或者删减内容。印刷书籍的出现则彻底改变了信息接收的途径,把相同的信息传递给所有人。印刷书或许不是信息传递的最佳方式,但它的出现成为历史进程中的新起点,自此以后,人们为阐明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得以继续。
最早出版的植物书是一本德语版的草药书,是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后的三十年间出版发行的。但是第一本植物学畅销书,新版的、热销整个欧洲的草药书则是奥托‘布伦费尔斯于1530年所著的《本草图谱》。布伦费尔斯本是一名加尔都西会的教士,后来成了路德教会的教师(同时他也是伯尔尼的医生)。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关键不在于它的内容,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由植物学之父——狄奥弗拉斯图和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季斯撰写的古典文本拼凑而成的。这本书的木刻印版由雕刻师汉斯‘魏迪兹独立完成的。与布伦费尔斯不同,魏迪兹不是一个复制者,书中的所有药草都是他根据现实生活中的样子画出来的。他创造了第一批植物印刷图像,其中包括睡莲、荨麻、车前草、欧龙牙草、马鞭草、白屈菜、琉璃苣、白头翁和麟凤兰花等,这些花在整个欧洲都可以被非常清楚地辨别出来。所以我们要说,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为欧洲植物学的发展铺平道路的是艺术家,而不是那些所谓的作家。
魏迪兹的榜样和老师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阿尔布雷希特·丢勒。丢勒曾经写道:“受自然的引导,不要丢掉这点,别指望自己抛开自然的引导还可以做得更好。你将会被引入歧途,因为真正的艺术就隐藏在自然之中,而且只有能够将它画下来的人才能拥有它。”对花卉的研究是对自然世界里那些令人惊奇的现实的快照,这些“照片”全都是在田问地头里直接拍摄的,所有植物的每个细节都被准确地记录下来——如报舂花波浪状的叶子,耧斗菜角状的花冠。但魏迪兹对此提出疑义,他认为描述的这些自然特征并不符合植物学的种属分类规律。此时此刻,在意大利,莱奥纳多·达·芬奇已经开始利用各类植物的不同肌理进行艺术创作。他曾尝试在不用木料,不用雕刻的方式,创造出木刻画的效果。比如,他曾将点燃的蜡烛置于树叶下方,火焰的不完全燃烧,会在叶子表面离析出一层碳颗粒,而后他把这些“碳叶”压在纸张之间,由此制造出一张张叶脉拷贝图,将复杂的叶脉构造呈现在观众眼前。达·芬奇所著的《论绘画》一书的第六章就是对植物,包括植物的根茎、枝干、树皮、花朵和叶子等部位的研究。
在艺术家的帮助下,文艺复兴时期的植物学家和自然学家们踏上了一条为植物命名的漫长跋涉之路。在比萨、帕多瓦和博洛尼亚,植物园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出现。因为被巴黎大学拒之门外,并被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和他的十字东征行动驱逐出安特卫普市的新教徒们变得愤愤不平。他们发现自己在英国处于错误的宗教阵营,于是聚集到法国南部蒙波利埃的著名医学院相互交换信息,随后又在北欧建立了新的中心。20万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离开法国,在瑞士、德国、英国和荷兰定居下来,这些人在佛兰德已经确立了他们作为知识渊博、极有天赋的栽培者和园丁的地位。这场宗教迫害行动也带来了一些进步,因为随着大批移民涌向欧洲,他们将更多有关植物的信息带到了那里,随之诞生了巨大的知识网络。像法国苗圃主人皮埃尔·贝隆这样的企业家从欧洲以外的地区带来了大量信息。1546到1548年之间,贝隆生活在黎凡特,出版了有关他的旅行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更加激起了欧洲园丁拥有这些奇特植物的欲望。
但是,随着每一波来自国外的植物的引入,挑选、描述以及将所有植物纳入理性命名系统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当各种各样的植物开始从美洲新建立的土地上涌入时,这项任务变得越来越急迫。西班牙人尼古拉斯‘莫纳德斯是第一个介绍那些生长在地图上没有明确标记的土地上的各种植物的人。1577年,他的书被翻译成了英文版本,名字为《来自新大陆的好消息》,其中介绍了许多新奇的事物,比如向日葵和烟草。给植物命名的工作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哲学家狄奥弗拉斯图时期就已经陆续展开,并且占据了欧洲许多杰出人士的重要精力。您下面读到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文摘
插图:
· · · · · · (收起)
读后感
所有的都是自然地一种属性,我们也不例外!在不断地追求自己的属性,想着昨天,看着今天,展望明天,自然……
评分一度喜欢植物图谱,根须浮在空气里,花是花,叶是叶,果实在旁陈列,有时候带个小小剖面图,一行我所不懂的拉丁文工整地签在留白处,好像在说:唉,告诉你你也不懂,不过还是告诉你吧,它叫Malus Transitoria。 啥? 需要细细研究、对照图片方才明白过来,此乃“花叶海棠”...
评分所有的都是自然地一种属性,我们也不例外!在不断地追求自己的属性,想着昨天,看着今天,展望明天,自然……
评分我指的是《植物的故事》(The Naming of Names:The Search for Order in The World of Plants by Anna Pavord) 看完全书,我甚至不知道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 是植物名称的历史演化? 是植物名称背后的有趣故事? 是各种植物名称的由来? 还是在寻访植物名称的历史中发生的有趣...
评分在书店看到的。纸质不错。图也超喜欢~~~~~~~~~~~~~~为啥这么有感觉叻?不由得想到了生物课本上的图的惨不忍睹。好囧。
用户评价
《植物的故事》这本书,对我而言,更像是一次与大自然的深度对话,一次对生命本质的探寻之旅。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情感的共鸣和智慧的启迪。书中关于“植物与人类的共生关系”的探讨,让我思考良多。我一直都知道植物对人类至关重要,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这种关系是多么的古老、多么的复杂,又是多么的相互依存。从人类早期依赖植物获取食物、药物,到如今植物在城市建设、工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植物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人类活动也对植物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书中对“过度砍伐”、“环境污染”等问题对植物造成的伤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呼吁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读到书中关于“植物修复环境”的案例,例如通过种植特定的植物来净化土壤和水源,这让我看到了植物强大的生命力和改造环境的能力,也让我对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充满了希望。更让我感动的是,书中还描绘了许多关于“植物的文化意义”的故事。从古老的传说到现代的艺术,植物一直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它们象征着生命、希望、坚韧和美丽,在不同的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读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植物的象征意义”,也读到关于“西方绘画中植物的意象表达”,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植物与人类情感的深厚联系。
评分《植物的故事》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认知体验,它让我看到了植物生命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和深邃智慧。书中关于“植物的睡眠与节律”的描述,彻底颠覆了我对植物“时刻保持活跃”的刻板印象。我曾以为植物只是被动地接受阳光和雨露,却不知道它们也有着自己的“生理时钟”,有着自己的“休息时间”。书中详细解释了植物的昼夜节律、季节性节律,以及它们如何根据环境变化调整自己的生命活动。我读到关于“睡莲”如何在夜晚闭合花瓣,保护自己的生殖器官,也读到关于“落叶树”如何在秋天“卸下”叶片,以减少水分蒸发,准备迎接寒冬。这种“睡眠”并非是生命的停滞,而是一种为了更好地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战略性休息”。它让我看到了植物们在生命活动中的精妙安排和深邃的生存智慧。书中还探讨了植物的“生物钟”是如何与地球的自转、公转以及月亮的周期相呼应的,这种与宇宙规律的紧密联系,让我不禁感叹于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评分《植物的故事》这本书,在我打开它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我与它之间一场别开生面的“邂逅”。它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将我拉入植物的生命洪流,让我感受它们的喜怒哀乐,体验它们的生存挣扎。书中关于“植物的防御机制”的章节,是我读过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我常常惊叹于植物在面对“敌人”时的“智慧”。它们不会像动物一样直接逃跑或反击,而是发展出了各种各样令人意想不到的防御策略。比如,有的植物会分泌有毒的化学物质来阻止食草动物的啃食,有的则会“伪装”自己,模仿其他有毒植物的外形。我读到关于“狼毒草”如何通过释放毒素保护自己,也读到关于“竹节虫”如何通过改变形态来融入环境,这些精妙的“伪装术”和“化学武器”,都让我对植物的生存智慧有了全新的认识。书中还详细解释了植物是如何感知并响应这些“威胁”的。它们可以通过气味、触碰,甚至是某些微生物的信号来判断危险的存在,并迅速启动相应的防御措施。这种“危机意识”和“应激反应”的能力,让我觉得植物并非我们想象中那样“被动”。它们也在积极地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世界进行着博弈。
评分《植物的故事》这本书,在我翻开它的那一刻,就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奇妙世界的门,让我沉醉其中,不愿离去。它用最真挚的语言,最深刻的洞察,描绘了植物们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让我重新审视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书中关于“植物的迁徙与传播”的章节,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一直以为植物是“原地不动”的,直到读到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它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一场场“生命远征”。从微小的孢子到巨大的种子,植物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巧妙的传播方式,以求将生命的火种撒播到更广阔的天地。我读到关于“椰子”如何在海上漂流,寻找新的栖息地,也读到关于“凤仙花”如何利用弹射的果实来“射击”自己的种子。这些充满生命力的“迁徙”故事,让我感叹于生命的顽强和对未来的渴望。书中还探讨了植物如何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它们在漫长演化过程中所进行的“基因交流”。这种跨越空间的“旅行”和“交流”,使得植物界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多样性,也让我对生命的韧性有了更深的理解。
评分《植物的故事》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植物的科普读物,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关于自然、关于我们自身存在的深刻反思。它用最朴实而又最动人的笔触,为我描绘了植物们的世界,让我感受到了生命最初的脉动和最蓬勃的力量。书中关于“植物的地下王国”的探索,是我最着迷的部分之一。我一直对根系充满了好奇,但这本书却将我带入了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神秘世界。原来,植物的根系不仅仅是固定植株、吸收养分的工具,它们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命网络”。书中详细介绍了植物根系的各种形态和功能,比如,有的根系可以深入地下寻找水源,有的则可以储存能量,还有的可以与其他植物形成共生关系。我读到关于“菌根”的描述,它们是如何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并且还能在植物之间传递信息,这让我看到了一个隐秘而又充满活力的“地下社交网络”。更让我震惊的是,书中还揭示了植物的根系能够感知土壤中的化学信号,并以此来判断是否存在危险或机会。这种“地下智慧”的存在,让我对植物的生命力有了更深层次的敬畏。
评分当我拿到《植物的故事》这本书时,我本以为会读到一些关于植物分类、生长习性的干巴巴的知识,但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完全错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是一种完全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让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由植物构成的宏大叙事之中。书中关于“植物的繁殖策略”这一部分,简直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一直对花朵为何如此绚丽,果实为何如此诱人感到好奇,这本书给出了我最满意的答案。它详细地解释了植物为了吸引传粉者——无论是勤劳的蜜蜂,还是翩翩起舞的蝴蝶——所演化出的各种策略。花朵的颜色、形状、香气,甚至它们分泌的花蜜,都是为了这场“生命之约”而精心设计的。而果实的出现,更是为了帮助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书中对不同植物繁殖方式的描绘,例如风媒、虫媒、鸟媒,甚至是通过水流和动物排泄物传播,都充满了趣味性和科学性。我读到关于“蒲公英”如何依靠风力播撒种子的故事,也读到关于“榕树”如何依靠鸟类传播种子的过程,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惊叹于生命的巧妙和自然的伟大。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书中还探讨了植物的“生命周期”与“死亡”的哲学意义。我曾以为植物的生命就是简单地生长、开花、结果、死亡,但这本书却让我看到,即使是生命的终结,也充满了意义。枯萎的落叶滋养了土壤,腐朽的枝干为新的生命提供了养分。植物的生命,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整个自然的循环。
评分《植物的故事》这本书,于我而言,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情感的共鸣。它让我看到了植物隐藏在静默外表下的勃勃生机,体验到了生命在不同维度上的壮丽画卷。书中关于“植物的能源利用”的描述,简直是让我对“光合作用”这一概念有了颠覆性的理解。我以前认为光合作用只是一个简单的化学反应,但这本书却将它描绘成了一场无比精妙的“能量收集与转化”的盛宴。从叶绿素如何捕捉太阳光,到淀粉如何储存能量,再到氧气如何作为“副产品”释放,每一步都充满了生命的奇迹。作者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将这些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解释得通俗易懂,让我仿佛亲眼看到了植物在阳光下进行的这场“生命工坊”。我读到关于“向日葵”如何精确地追踪太阳,以获取最大化的光照,也读到关于“浮游植物”如何默默地为地球提供一半以上的氧气,这些细节都让我对植物的“能量智慧”充满了敬意。书中还探讨了植物如何利用这些储存的能量来支撑它们的生长、繁殖和防御,将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延展成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故事。
评分《植物的故事》这本书,着实带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植物的百科全书,更像是一部充满哲学思考和生命哲理的诗篇。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植物的感官”这一章节的论述。我们人类习惯于用自己的感官去理解世界,而植物,它们又如何感知周遭的环境呢?作者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生动的案例,向我展示了植物们并非“迟钝”的生命体。它们可以通过根系感知土壤的养分和湿度,通过叶片捕捉阳光的强度和方向,甚至能对触碰、声音和化学信号做出反应。我曾以为植物只会默默地生长,直到读到书中关于“捕蝇草”如何精准捕捉昆虫的精妙设计,以及“含羞草”在受到触碰时叶片迅速闭合的反应,我才意识到,植物也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感知”能力,它们以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与这个世界进行着互动。这种对植物“感知”的重新定义,极大地拓宽了我对生命形式的认知。书中对于植物之间“交流”的描述也让我大开眼界。我从没想到,植物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沟通网络。通过根系分泌的化学物质,或者通过真菌菌丝的连接,它们可以传递信息,警告同伴危险,甚至分享养分。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人类社会的交流方式,而植物之间的这种“无声的语言”,却显得更加原始而纯粹,充满了生存的智慧。我常常在阅读时,会不自觉地将书中的知识与我身边的植物联系起来,当我看到一棵熟悉的树,或者一朵路边的小花,我都会用新的视角去观察它们,去想象它们可能正在经历的一切。这种阅读带来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却又深刻而持久。
评分《植物的故事》这本书,在我看来,简直是一部关于生命奇迹的宏伟史诗。它以一种极其人性化和富于情感的方式,将植物们的世界展现在我眼前,让我仿佛亲身经历着它们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生长,每一次蜕变。我尤其对书中关于“植物的记忆与学习”这一部分的内容印象深刻。我曾以为植物是缺乏记忆和学习能力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书中通过大量的科学证据和生动有趣的实验描述,让我看到了植物们令人惊叹的“智慧”。它们能够记住光照的周期,能够识别土壤中的危险信号,甚至能够“学习”并适应新的环境。例如,书中提到了一些植物在受到反复的模拟“危险”刺激后,会产生一种“免疫”反应,这与我们理解的学习和适应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对植物“智慧”的发现,彻底颠覆了我以往的认知,让我对植物的生命力有了更深层次的敬畏。书中对“植物的进化与多样性”的阐述也极具吸引力。作者并没有枯燥地罗列植物的分类,而是通过讲述不同植物在漫长演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和机遇,将植物的多样性呈现得淋漓尽致。我读到了关于“蕨类植物”如何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也看到了“被子植物”如何在后来的演化中脱颖而出,成为如今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类群。每一个植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进化史,都充满了生命为了生存而付出的努力和智慧。
评分一直以来,我对自然界充满了好奇,尤其是那些静默生长,却承载着无尽生命力的植物。偶然间翻开《植物的故事》,我便被深深吸引,仿佛踏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妙世界。这本书不像我以往读过的那些枯燥乏味的科普读物,它以一种诗意而生动的方式,为我揭开了植物们不为人知的生命历程。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初读到关于“沉睡的种子”那一章节时,内心的震撼。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种子,它们如何在黑暗中积蓄力量,等待着一个恰当的时机苏醒。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份生命的韧性,它们并非被动地等待,而是在静默中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役,对抗着时间和环境的考验。当春风拂过,雨水滋润,它们便如同被唤醒的精灵,舒展腰肢,探出嫩芽。这一过程,被描绘得如此富有张力,让我对生命的奇迹有了更深的理解。书中关于植物如何适应环境的描写也让我印象深刻。无论是沙漠中顽强生存的仙人掌,还是深海里摇曳生姿的海藻,它们都有着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作者没有简单地罗列它们的特征,而是深入挖掘了它们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独特机制。比如,我曾对那些生活在极度干旱地区的植物如何储水感到好奇,书中便详细解释了它们厚实的叶片、发达的根系以及特殊的代谢方式,这些精妙的设计,无不体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阅读的过程,更像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仿佛能听到远古植物的低语,感受到它们在亿万年的演化中留下的印记。书中对不同地域植物群落的描绘也极具画面感,仿佛将我带到了亚马逊雨林的神秘深处,亦或是喜马拉雅山脉的皑皑雪峰,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不同生态系统下植物的多样性与壮丽。
评分美图
评分就是对图感兴趣一点,内容觉得不是很好。。。
评分美图
评分插图漂亮得要死!!!
评分很多人把视角放在植物本身,这恐怕是书名翻译的问题,但是作者却是利用人们对植物认知的历史去阐述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图书下载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