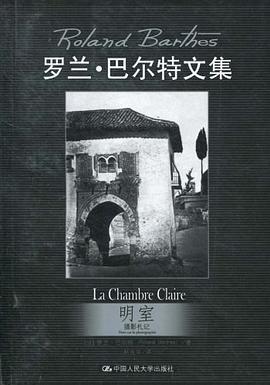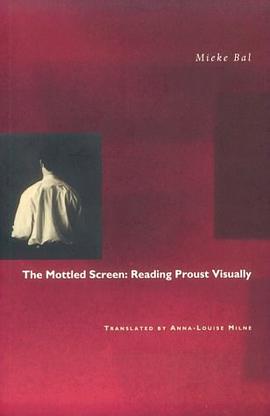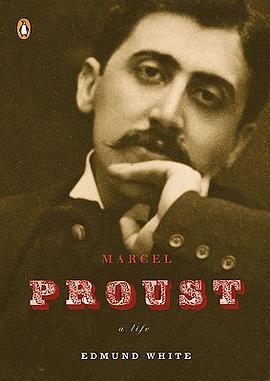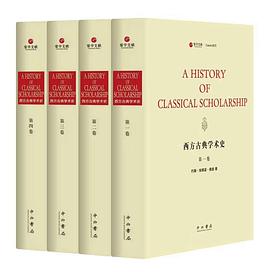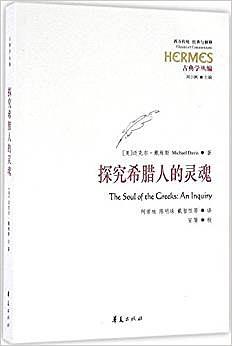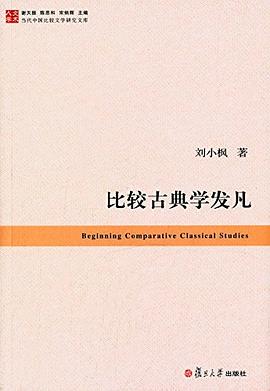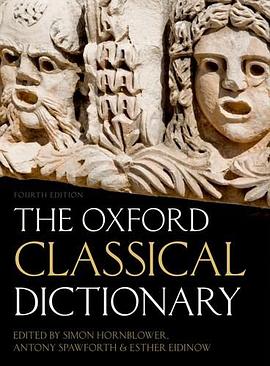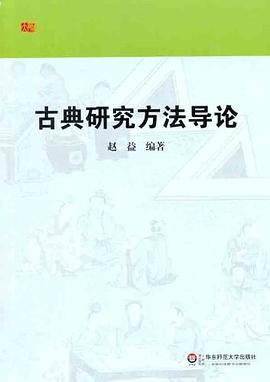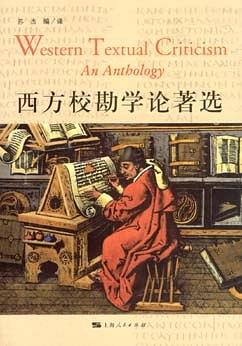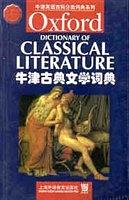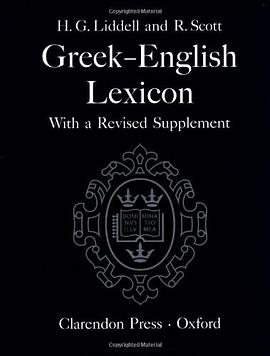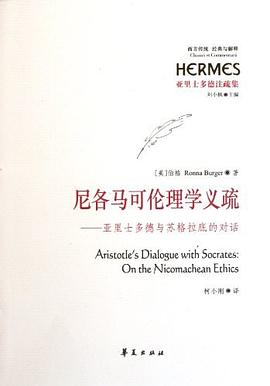第一章
一
——喂!这儿没人吗?布拉斯!该死的!这里的人都聋了吗?布拉斯!
——别大声嚷嚷,对你没什么好处,阿罗尔德。
——你死到哪里去了?我在这儿一个小时了。
——瞧瞧,你的马车破成什么样子了,阿罗尔德,你不要这样到处丢人现眼。
——别管我的马车,你先拿着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布拉斯。我怎么知道。是个包裹,一个寄给瑞太太的包裹。
——给瑞太太的?
——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
——给瑞太太的包裹……
——听着,布拉斯!你愿意拿着它吗?我得在中午前回到桂旎葩。
——好吧,阿罗尔德。
——交给瑞太太,拜托了……
——交给瑞太太。
——好啦,布拉斯,别像个傻小子。时不时也到城里来逛逛,总待在这里你会烂掉的。
——你的马车真看起来真寒碜人,阿罗尔德。
——好啦,再见啦!好好干,小伙子,走吧……再见,布拉斯!
——嗨,如果是我驾那辆车,我就不会跑太快,阿罗尔德!我就不会跑太快。那辆车也跑不快,真寒碜,一架破马车。
——布拉斯先生……
——看起来好像走几步就会散架……
——布拉斯先生,我找到了,我找到那段绳子了。
——真能干,皮特。把绳子放在马车里。
——绳子在麦地里呢,开始没看到。
——好吧,皮特,你现在到我这里来。放下那段绳子。过来,孩子,我要你现在回家去,立刻过来,你听到了吗?拿着,拿着这个包裹。跑去找玛格,把这包裹交给她。听着,告诉她,这是给瑞太太的,好吗?你这样跟她说: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从很远……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你得这样说。
——从很远的地方,好吧。
——去吧!跑着去……边跑边重复,这样你就不会忘。赶紧去吧,孩子。
——好吧,先生。
——大声重复,这个方法很管用。
——好的,先生。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
——跑着去,我说过了,要跑着去!
——……从很远的地方寄来,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给瑞太太的……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很远……这个包裹……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从很远的地方……不,昨天到的……昨天……到的……
——嘿!皮特,你是不是中邪了?你要跑到哪里去?
——你好,安奇……昨天到的……我在找玛格,你见到她了吗?
——她在厨房里。
——谢谢!安奇……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昨天到的……好像是……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从很远……这个包裹……您好呀,哈普先生!……是给瑞太太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瑞太太……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玛格!
——小家伙,什么事?
——玛格,玛格,玛格……
——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皮特?
——一个包裹……是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
——让我看看。
——等一下,这个包裹是给瑞太太的,是昨天晚上到的……
——怎样?皮特……
——……昨天晚上到的……
——……昨天晚上到的……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到的,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寄来的。
——好像是很远的地方?
——是的。
——让我看看,皮特……好像是很远的地方……这上面写满了字,你看见了吗?我觉得一定能知道从哪儿寄来的。过来看看,施蒂特,有一个给瑞太太的包裹……
——包裹?说来听听,很重吗?
——好像是从远处寄来的。
——别闹了,皮特。包裹很轻,很轻,你说呢?施蒂特,你不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份礼物吗?
——那谁知道呢,说不定是钱呢。或者是有人恶作剧。
——你知道女主人在哪儿吗?
——我看见她向房间走去了。
——好啦,你待在这里,我上去一下。
——我可以跟你去吗?玛格。
——来吧,皮特,别磨蹭。我很快回来,施蒂特。
——是个恶作剧,我看就是个恶作剧。
——会是个恶作剧吗,玛格?
——那谁知道,皮特。
——你知道的,但你不想说,是不是?
——我就是知道也不跟你说,就不告诉你。关上门,得了吧。
——我不会说出去的。我发誓。
——皮特,听话……以后你也会知道的,你会见到……或许将会有一个节日……
——一个节日?
——差不多吧……如果,里面有我想到的东西,明天将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或者后天……或者过几天……总会有个特殊的日子……
——一个特殊的日子?为什么说是特殊的?
——嘘!待在这儿别动,皮特。不要乱动,行吗?
——好吧。
——不要动……瑞太太……对不起,瑞太太……
这时,就在这时,瑞蓉从书桌前抬起头来,她把目光投向闭着的门。瑞蓉,瑞蓉的脸。桂旎葩的女人们在照镜子时会想着瑞蓉的脸。桂旎葩的男人们在注视自己的女人时也会想着瑞蓉的脸。她的头发,她的颧骨,她洁白的肌肤,她的眼帘。除了这些,最生动的是她的嘴:无论是鄢然一笑,还是大声叫嚷;无论是沉默不语,还是顾盼流连。瑞蓉的嘴总能让你心神不宁,它很轻易地就能勾起你的幻想,扰乱你的思绪。“有一天,上帝描绘了瑞蓉的嘴,就在那里,人们产生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原罪感。”蒂克特是这样描述的,他在神学院做过厨子,对神学略知一二,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别人都说他以前工作的地方是个监狱,他反驳道:“笨蛋,那还不是一回事。”人们都说那张脸难以描述,自然是指瑞蓉的脸。她的脸已经在人们的想象里根深蒂固。现在这张脸就在那里,就在那儿,对着关闭着的门。这一刻,她从书桌前抬起脸来,对着关着的门说:
——我在这里。
——这儿有您的一个包裹,太太。
——进来吧,玛格。
——有个包裹……是给您的。
——给我看看。
瑞蓉站起身来,接过包裹。她看了看用黑墨水写在牛皮纸上的名字,把包裹翻转过来,抬起头,眨了一下眼睛,重新看着包裹。又从书桌上拿过一把裁纸刀,割断了绳子,把包裹拿在手里。撕开牛皮纸,露出白色的包装纸。
玛格往门边倒退了一步。
——别走,玛格。
她撕开白纸,下面是一个玫瑰色纸包着的紫色盒子,紫盒子里有一个绿色布面的小盒子展现在瑞蓉的眼前。她打开绿盒子,看了一眼,不动声色地合上。然后她转向玛格,微笑着对她说:
——瑞先生快回来了。
就这样。
玛格跑下去告诉皮特,“瑞先生快回来了”。蒂特喊道:“瑞先生快回来了。”所有的房间都回荡着“瑞先生快回来了”,直到有人从窗口喊了一句:“瑞先生快回来了!”“瑞先生快回来了”。这句话一直传向田野,“瑞先生快回来了”;这消息从一片田野传向另一片田野,一直传到河边,听到有人大喊一声:“瑞先生快回来了。”声音很大,玻璃厂都有人听到了喊声。他们奔走相告,瑞先生快回来了。就这样,所有人都议论纷纷。炉窑那里噪声比较大,以至于有人不得不提高了声音问:“你们说什么?”“瑞先生快回来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连有点耳背的伙计都知道了这条消息。“瑞先生快回来了”,这消息如雷贯耳。瑞先生快回来了,啊,瑞先生快回来了。总之,像一场爆炸响彻云霄,回荡在人们的心里、眼里,一直传到桂旎葩:距这里一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没过多长时间,人们看见奥里威一路跑来,他下马的时候没踩准蹬子,一下子滚到地上。他嘴里骂骂咧咧的,一手拣起他的帽子,屁股还在泥里,小声嘟囔着,好像他掉下来时把那句话也摔坏了,摔得漏了气,粘了土。他自言自语道:“瑞先生快回来了。”
瑞先生时不时回来。他通常都是在离开一段时间以后回来。这件事情体现了他的内心状态,也可以说,体现了他的心绪。瑞先生办事情总是有板有眼。
很难理解他为什么有时候会离开。从来都没有一个真实可信的理由来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没有特定的季节和日子,也没有特定的情况。很简单,他说走就走。他用几天的时间准备大大小小的东西:马车、信件、行李箱、帽子、旅行书桌、钱、证件,诸如此类。他不停地整理,通常都是面带微笑。每一次都像一只无头苍蝇,投身到这种繁杂的家务中,充满耐心地瞎折腾一气。这种活动
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如果不是最后那个必然时刻的到来。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仪式,几乎难以察觉。这个仪式只在心里进行:他关掉灯,和蓉待在黑暗中,两人默默地并排躺在床上;在不安的夜里,她任时间白白地流逝,然后闭上眼睛说:
——晚安。
又问:
——你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蓉。
第二天,他出发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连蓉也不知道。有人说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有人列举了那年夏天那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他八月七日早上出发,第二天晚上就回来了。脸色平静,带着七件没有拆开的行李,好像在做天下最平常不过的事情。蓉什么也没问,他什么也没讲。仆人们忙着卸行李。生活在短暂的迂回之后又重新启动了。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