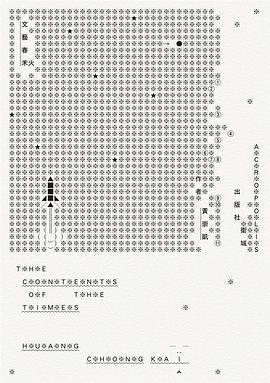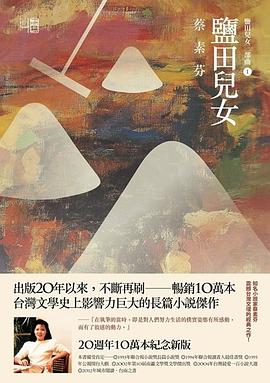推薦序/魔幻手指──讀《文字手藝人》有感 ◎簡媜
自序/這本書獻給所有喜愛副刊的人
楔子/心在高原上──記我大學畢業的一九八六
卷一/副刊的前世今生
審稿
多年來,我深深體會,「審稿」這件工作,面對的終究不是「稿」,而是人,一切冷暖只能放在心中。
投稿
周公送詩過來,我下樓取稿,他一定要重重地握手(好痛喔!)同事們取笑說:「周公是專程來看妳的啦。」
退稿
做主編,要有被討厭的勇氣,是我以點點滴滴親身遭遇,從這個職場上學到的一件珍貴的功課。
催稿
「你最想暗殺的人是誰?」,有九位痛快回答:「作家!」為什麼呢?同文裡寫到「編輯八恨」,第一恨便是「作家黃牛,沒交稿」。
連載
我趕上的兩大報連載是金庸,在聯副的《連城訣》,在中時人間的《倚天屠龍記》……在吃緊的生活費裡,從不吝惜保留訂報的習慣……
稿費
副刊所剩無幾,要以稿費養家活口,根本不可能。我同時是作家也是編輯,比誰都嚮往過去的好時光……
副刊的源起
把夾在新聞之中「補白」的詩詞雜文移至篇末,與新聞、評論、廣告做出區隔,這個放在報紙篇末文藝性的區塊有什麼特別的稱呼嗎?曰:報屁股。
卷二/台下風景
電話!
電話,我真的怕接電話!從事副刊編輯以來,接過各式奇奇怪怪的電話,可惜沒有一一記錄下來……
編巫
編版過程中無心插柳的小趣味,俯拾即是,常令我覺得「版面」這個東西,自有它的磁場,好像主編之外,還有另一個主編。
煙絲披里純
在砧板上快刀切磋,大鍋上翻攪潑撒,熏蒸迷霧裡念想青春繁華,我想,我可能是副刊史上第一個真正以正宗炊煙做為煙絲披里純的主編。
林海音與琦君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難處。而在近年種種喧囂之中,我常常問自己,該如何自處?林海音的寬容,永遠是暮鼓晨鐘。
憶陳之藩先生
信裡提到楊振寧教授給他的短箋,應考慮為公眾人物的信;我想,陳之藩先生給我的傳真亦然,是該公開、記錄下來的。
抓bug
Bug本是小蟲子,我立刻聯想到我的工作,這一生有大半時間在面對版面上的小蟲子──那些標點符號。
老
我閱讀他們的作品,從中獲益成長,稱老師並不為過,也不會有人因為被叫老師而翻臉的。「老」字放在師上,最讓人安心。
台下風景
編輯,猶如劇場裡的後台工作,台上看到的是一篇篇經過梳理、校對、配上插畫、攝影,編排後的作品,台下看到的,有時不僅是作品,更是人。
這玩意兒我家很多!
七年來,我「逛」了數十位作家的書房,這成為我與作家另一形式的交往,讓我對作家有不同角度的觀察,比坐在咖啡館裡聊天也許更深刻。
專業與敬業
一聽到叫我副主任、副座的,只要再多交談一兩句就知道,他從頭到尾就不知道報紙有一種版面叫作「副刊」……
是因為費用的關係嗎?
我曾開玩笑跟一位小說家說,乾脆我們以後互相扮演對方的助理吧,就可以果決幫對方拒絕掉太無理的邀請,而不會什麼都不好意思問……
大廚就是這樣?
究竟怎麼樣退才叫作婉退?我知道:敘述枯燥、理路不通、文字囉嗦、彆扭、俗套、老生常談、不知所云等等的實話、大白話絕不可以說。
懇請不要
懇請不要一直問、一直問!問某篇文章為什麼不用?問稿子何時刊登?問為什麼很久沒見到某某作家的文章?(天知道為什麼!)
卷三/給下一輪副刊盛世的備忘錄
手藝人
許多手藝人一環扣一環,把每一個版,都當作一個工藝品精雕細琢而成。這是編輯對作家、作品的心意,也是對讀者的誠意。
副刊、武俠、溫世仁
我與武俠緣分真的不淺。我進聯副之前,曾在明日工作室任職,與溫世仁先生有短暫的相處,那是令人懷念的時光……
副刊與諾貝爾文學獎
戒嚴年代,副刊是報紙中最自由曖昧,得以文學包裝、夾帶反抗思想……那是封閉的台灣,眺望世界的窗口,以文學之名。
專題的兩難
我心中的理想副刊,是海……至少必須是江河,有波瀾,有激流,因此編輯需
要盱衡局勢,扣緊社會的脈動。
數位匯流
許多潛伏網海的優秀書寫者浮出水面。對我而言,文學遊藝場,像是網路與副刊這兩個平行宇宙間,一個交會流動的出入口。
副刊家族
在我心中,聯副、繽紛、家庭,是三足鼎立的關係,菁英性格、庶民性格,再加一點婆婆媽媽,有時互補,有時交融。
最享受的事
那一年繆思的星期五開場,主持人陳義芝說:「將來大家會記得,在二十一世紀,台北有一個美麗的文學景點,帶動了文化的動能。」
極短篇與聯副
這是一場小說的極小化實驗,網路時代裡,更便於在手機上閱讀,是否可能成為新一波的全民寫作呢?
文學獎
文學獎的意義,當年還不僅在於拔擢新秀、培養作家,也成功扮演了突破言論尺度、意識型態、挑戰禁忌、衝出社會常軌的先鋒。
拜訪十年後的副刊主編
親愛的副刊主編,十年後,以我的生涯規畫,必不在這個職場上了。……而我是這樣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我有信心,十年後,花園還在。
跋/編輯自己的人生◎許悔之
附錄/編輯檯上
收回
序
推薦序
魔幻手指
——讀《文字手藝人》有感
◎簡媜
有兩個字,對我具有吸引力︰一是稿,另一個是編。這兩個字非常美,別問我為什麼,天底下有些事沒有為什麼。
先說稿。我在每年必定淹水的偏僻小學四年級認識它,不是來自課本或老師偶開天眼要在五穀六畜之外教涎涕小童一個他們一生都用不到的字,而是來自一份叫「國語日報」的報紙。我是負責拿報紙的人,也知道這報紙一旦進了教室就會無影,所以一拿到手立刻閃入校園一處隱密的夾壁讀報,直到打鐘才跑回教室,因此練出速讀與跑步。
看久了,生出那年齡不該有的羨慕。我對在報上刊登作文很感興趣,注意到「投稿須知」,猜想寫文章「寄」給他們就叫「投稿」——以我當時的智能,不明白為什麼不叫「寄稿」卻叫「投稿」?我確實這樣幻想︰難道要跑到台北報社,把文章捲一捲綁個石頭朝窗戶「投」進去嗎?不過,最困擾我的卻是「不可用筆名」這一條;我沒敢問老師「筆名」是什麼意思,因為「投稿」這件事必須秘密進行,我年紀雖小,卻知道要擁有一點秘密像擁有私房錢一樣,生命才有獨享的滋味。以我當時的智能理解,以為「不可用筆名」就是「不可用筆寫名字」,不用筆用什麼?想破頭,終於想到解決辦法,而且付諸行動。我不想在此透露那辦法,以免傷了小四女生的自尊心,雖然她已不存在,但她對我有恩。如果不是她那麼單純又勇敢地進行一次跟「稿」相關的軍事秘密行動,我不可能在平靜六年之後,於高二那年猛然記起跟「稿」的戰事還沒打完,而且這回玩真的,火力全開。
再看一眼,稿,這個字有魔力。從禾高聲,即使不明瞭「高」這個聲音怎麼跟結實穀物發生關聯,也不妨礙想像那場面︰有風月夜,落拓的你獨自走在無人小徑,忽然,一望無際飽滿的禾田,只對你一人發出要求收割的尖叫聲。你怔住,沒有選擇,這樣強烈的召喚必須回應,你躍入田裡,領取屬於你的豐收。稿,從乾稻草原意繁衍為文書稿件此等心靈糧草之稱,想來也是契合的。既然是心靈禾稈,當然要向「投海自盡」這個連命都不要的成語借一個「投」字來用,方能顯出重量,也才能呈現「投稿」後被「退稿」那種類似被滅口的痛苦與不共戴天的憤怒。不信的話,請先讀本書〈退稿〉那篇,就能明白被退稿的那種憤怒幾乎可以用來發電。
我是看副刊長大的,不,這句話太誇大,應該說,我是懷著對副刊的憧憬長大的。在無字鄉間,阿嬤從羅東鎮上買回碗盤什物,用來包裹的報紙對我而言就是文字蛋白質,轉骨良方。曾經聽聞一艘遠洋船上只有一張報紙,幾個水手輪流借讀,每天讀了又讀,彷彿新的一般,以度過漫長航程。我乍聽這迷人的海上奇幻漂流,立刻想起自己的讀副刊經驗;讀第一遍,讀的是作者筆下的作品,讀第二遍,字、句、段落開始裂解,自己的幻想、情懷四處滋生,與之激蕩起來,讀到第三遍,根本可以下筆寫文章了。真不知那群水手讀的是誰的文章,若恰好是女作家,她在他們心中的地位很有可能接近媽祖。
在紙本「報紙」越來越像空中飛翔的老鷹滑向晚霞的此時,讀到大思想家梁漱溟(1893--1988)自述自學小史,感觸特別深。他寫道︰「我的自學,最得力於雜誌報紙……作始於小學時代,奇怪的是在那樣新文化初開荒時候,已有人為我準備了很好的課外讀物,這是一種《啟蒙日報》和一種《京話日報》……」到了中學,梁漱溟自述︰「我擁有梁任公先生主編之《新民叢報》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和同時他主編的《新小說》全年一巨冊………稍後更有立憲派之《國風報》,革命派之上海《民立報》……這都是當時內地尋常一個中學生,所不能有的豐富資財。……由於注意時局,所以每日的報紙如當地之《北京日報》《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等,外埠之《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讀物。談起時局來,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個中學生。」
如果梁漱溟還活著且人在台灣,當他知道學生早就不看報了,不知有何議論?他吹鬍子瞪眼說出的一百個必須讀報的理由,自有一百零一個網路留言反駁他,更有一個「當官兒的」直接砍了預算稱之為專業問題專業解決。
在數位洪流淹沒了生活的現代,回想「紙本報紙」的身影,有點像是我們這一代的「寶可夢」——風雨交加的早晨,不惜撐傘出門去雜貨店買報紙,因為對鉛中毒甚深的人而言,不翻開報紙不知道怎麼開始這一天!鉛毒中最嚴重的是「副刊癮」,報禁時期三大張糧草,一日不讀副刊,那日便心神渙散(有連載時更嚴重),極容易做出錯誤決定,譬如跟一個不值得愛的人盲目約會留下遺憾。
另一個具有致命吸引力的字是「編」,許多作家逃不出它的魔掌。這個字雖含有「被蹂躪」成分與「自虐」傾向,更重要是具有頑強地欲完成某件事物與他人分享的企圖心,活在「利他」的想望裡。通得過的從此擁有魔幻手指,能點石成金,為社會帶出澎湃的新思潮、迷人的藝文濤浪。
以文字手藝人自詡的宇文正,用爐邊閒話的家常口吻,娓娓道來編輯檯上不為人知的副刊樣貌與戰況。這由作者、編者、讀者、評者四合一組成的獨特江湖,雖有波濤凶險之處,亦有景致宜人之時。透過她那溫婉且詼諧的筆觸,那凶險之處讀來別具浮世趣味、人性考察,而景致宜人的部分則不免引發我輩緬懷——我們熱騰騰的青春,曾經用報紙副刊包覆著,沾了洗不掉的油墨,以至於在青春已然熄止的此時,仍會因文字的烙印而微微感到心痛。
一張副刊,會不會隨風而逝?在副刊上掀起潮浪的新秀或老將會不會蒸發?所有依附在「稿」與「編」這兩個字的那群人會不會成為飛揚的沙塵?
也許會,也許不會。我樂於想像,每一世代都會有新崛起的文字手藝人,他們堅毅地朝著不可理喻的社會,伸出魔幻手指。猶如我們無限景仰、開創副刊王國風雲的瘂弦與高信疆,猶如在最壞年代、到處是拉下鐵門的聲音,而她仍然護守副刊本舖、儼然將成為旗艦店的宇文正。
跋
編輯自己的人生
◎許悔之
常常我都覺得自己是活在另一個世界的人,像是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的電影《永遠的一天》(Eternity and a Day)裡,那一個心思永遠飄忽在想像中的詩人。
從小孩時候喜歡閱讀,少年時開始喜歡寫詩、寫作,年輕時開始做了編輯,我這半生基本上完全與文字為伍。有時抽一根菸,是在想一個書名,有時咖啡館裡坐著,是在想一段文案,不管路上如何塞車,開車的我通常不會覺得無聊,有時聽聽音樂,有時把《金剛經》從頭想一遍,有時想想某一位作家的書還應該補上什麼內容……,時間一下就過了,完全忘了路上在塞車,我像是一個腦袋中裝滿了文字的人,腦袋就是我的煉丹爐,有時文字契合了想像,甚至更為精美的迸現,那個時候,我總是覺得自己是孫悟空──火眼金睛,觔斗雲一翻十萬八千里。
我是那個《永遠的一天》裡的詩人,永遠是這個現實世界的「叛徒」。
一個喜歡文字的人,跟一個喜歡數學的人,嚴格說來並沒有不同,喜愛到了深刻就變成了偏執,所以我才會在法國菜餐廳對著經理說:「菜單上的scallop,多了一個『o』喔!」或者帶著小孩去宜蘭看黃春明先生的兒童劇,住在一個舒服的民宿裡,我整夜為了他們的宣傳DM太多錯字而急著要找老闆說明。這種偏執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強迫症?希望每一個字和詞,都能精準、精妙,而且餘味無窮,而且彷彿這一段話、這一篇文章、這一本書,真的能改變一些人、給別人一些什麼。那種感覺夾雜著夸父追日的悲壯,完成度好的時候,會以為自己是某一種造物者,把虹放在了雲彩之中。
宇文正,我都習慣叫她瑜雯,當然和我相同的部分,都是從小對文字偏執,她和我說過在讀景美女中的時候,怎麼坐在公車上讀《紅樓夢》,還有其他的雜書、閒書、文學書,渾然不知聯考將至。我知道那種感覺,一篇文章或一本書,也常常催眠了我,我讀著讀著渾然不知老之將至,讀完之後,像是從催眠之中醒了過來,這個世界變得雨後草色新,山巒白雲歷歷在目。
但瑜雯又是和我不一樣的人,她們家小孩念高中的時候,她做了三年的便當,還以此完成了一本動人的書,她是很少數創作力充沛又能顧好小孩、享受家居的人,她寫了很多文章,和朋友相聚、歡宴,也常常去擔任評審,並參加各種活動,我不知道她怎麼可以把這一切平衡得那麼好!彷彿她在一天之中有多了我好幾倍的時間。
我們兩個都是五年級生,都在台北廣義的文化圈中追尋自己的志趣,並以此維生,四五年級生──有許多寫作的人,都加入了編輯的這個行業,因為寫作彷彿不足以維生,編輯遂成為我們這樣的人,平衡理想與現實的道路。
瑜雯是少數在編輯界工作多年,仍保持赤子之心的人,每次聽她津津有味地談著一篇文章、一位作家,我都覺得她如此興味盎然,像是昨天才剛入了行的人;很少的時候,我也聽過她講了一些在編輯遇到的煩惱事、不平事,但通常她都是實事求是地訴說之,我不曾聽過她用敵意的語詞去敘述那個使她煩惱的人或煩惱的事,但其實瑜雯和我一樣,都是「資深編輯」了,那意味著我們在以編輯為職業兼志業的人生裡,已經工作了不少時日,認得不少的人,經歷了不少的事。
我有時見到她,會升起一種感慨,她怎麼可以把「文字」和「現實」過得這麼好、這麼平衡?因為我知道文字源於現實,又常常超乎了現實……。
所以當我看到《文字手藝人:一位副刊主編的知見苦樂》完整的稿件時,忍不住一讀再讀,順便回顧了自己的前半生,那在編輯裡追索的我,有多少的榮耀,還有多少的挫折,有多少的欣悅以及傷口。
做事不容易,做人更難,尤其是擔任重要的編輯人,總是要面對各方壓力、各方需求,有時候退了一篇稿子,就結了一個「冤家」;我這半生做過副刊主編、雜誌社總編輯、出版社總編輯,中年的時候創立了一間出版公司,有時朋友問我感想,我總忍不住犬儒地說:「做了編輯多年,朋友三百,仇家七百──」
用稿、退稿、邀稿、看稿、修稿、下標、企畫、配圖、設計、清版……,一位編輯,尤其是一位副刊主編,每天的那塊版面就像是一艘船,要從此岸渡到彼岸,有些沒上船的人,在岸邊不平咒罵,有些上了船的人,或許會嫌沒有坐在好的艙位……,副刊主編像是船長,總是要面對各種乘客、各方期望、各種眼光、各種評價,終究這個世界是沒有皆大歡喜的,所以船長要有很雀躍的心,能夠把每一天的版面(航程)當作全新的航行;船長也要有望遠的眼光,能夠把船開到新的景點;船長也要有堅強的心和廣闊的肚量,可以面對、忍受不同的看法和聲音。
而這一些,瑜雯都做得遠遠、遠遠的比我好!在台北文壇、文化圈,幾乎沒有聽過她有什麼「仇家」,而且她把編輯的人生過得平衡而且陽光、而且美好,而且她把副刊的每一天版面,編得如同一艘美麗且堅固的船,而且她還創作不斷,寫出了好多好多美好的文章……。
所以《文字手藝人:一位副刊主編的知見苦樂》不只是一本讀來津津有味的談編輯之書,而且也談論了人生、談論了人間行走的平衡,更談論了美好的心量。這本書裡的敘述者,同時兼有老靈魂和少女心。
如果你是從事編輯相關工作的人,無論是紙本或者數位媒體,那麼我覺得你應該讀讀這本書,鑑往知來,不管載具如何改變,只要文字存在,編輯這個行業便永不會滅亡。如果你是喜愛文字的人,那麼你更要讀這本書,因為擁有對文字的執念和喜愛,宇文正不但在創作裡是一個美麗的新娘,也完美地為他人「作嫁衣裳」。
瑜雯不必做這個世界的「叛徒」,她把文字和編輯完美地和這個世界同頻率、共生息;把不一定美的人事編成美的版面,把美好的書寫編成更美的人生──這本書中她說的,其實是如何編輯自己的人生吧。
自序
這本書獻給所有喜愛副刊的人
我書稿完成後向來不愛寫序,總怕落了言詮,想表達的,都在書裡了啊,若出版社有此要求,我經常另寫一篇貌似隱喻的散文,充作自序。這是第一次,完稿後我主動告訴出版社總編輯:我還要寫篇序,我想要感謝很多人。
我的人生在擔任副刊主編之後,有了很大的轉變,並且那轉變是直接挑戰我的個性的。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怕吵、怕鬥、怕拒絕、怕囉嗦的人,最好是一輩子默默寫作,或是就做個專業編輯,凡事上頭有人頂著,我便可無憂無慮,私下持續寫著自己的小說,有人願意出版,有一點點讀者,就會很快樂了。
小時候我跟二哥吵架,一邊哭,一邊痛訴委屈,就在我張大嘴巴涕泗縱橫之際,二哥凝視我的臉,很嚴肅地說:「妹你不要一邊哭一邊罵人,真的真的很醜!」是童年種下的創傷嗎?我長成一個一遇見爭執就想逃避的人。我是籃球場邊的張大帥,搶什麼?一人發一顆球給他們不就好了嗎?
民國九十六年七月,我的上司陳義芝退休,到師大教書去了。他在半年多前曾發一封email給我,信的主旨寫著:「秋天的消息」,我心想詩人主任就是這樣風雅,給下屬寫個email還說是「秋天的消息」。閱信後卻讓我愣住了,他提早讓我知曉他的生涯規畫,並且囑我接下副刊的重任,希望我有心理準備。
半年多的「心理準備」無論如何是不夠的。我嚴守祕密,不曾向任何人透露,因此在義芝退休,我接下主任職務時,對外界而言頗為突兀。家有幼兒,我不常在外應酬,且那時我外表貌似年輕,便輾轉聽到許多前輩作家議論:聯副怎麼會讓一個小女孩來接主編?一時間,真覺得自己毫無武功、忽被推為掌門,內心惶恐難以言說。
轉眼近十年,我認真對待這份工作,深切明白它不是一個職務,不是一個「位子」,它是倘若有心,確實可以為作家做一些事,可以為文學留一點什麼,可以為「副刊」這個獨特的園地,創造一片景致的任務。我慢慢摸索出生活、工作的節奏感,經常思考副刊還可以「做什麼」。必須對應稿件,對應事務,更對應許許多多的「人」,我的天性在這些過程裡備受考驗。也許因此,心理上,老以為自己剛接下重任不久,走進作家群聚的場合,內心始終害羞,不自在。當時任《幼獅文藝》主編吳鈞堯提議我寫「副刊學」專欄時,我馬上推卻:「你去找資深的主編吧。」「妳就很資深啊!」原來我已經很資深了啊?
真的謝謝鈞堯的提議,否則我不會動念去疏理自己的編輯生涯,思索副刊在這個時代裡的意義;許多編輯檯上、檯下的趣事、美事、憾事也因此重新憶起。尤其經過這個書寫的過程,我對副刊有了更多、更積極的想法。
也謝謝悔之和有鹿的朋友們,從開始在臉書上轉載,他們便緊盯著這個專欄,督促我撰寫成書。
還有我親愛的副刊同事們:開平、婉茹、盛弘、立安、姵穎、胡靖(咦,按年齡序?),以及前兩年告別副刊返鄉實踐在地文化工作的小熊、更早離職的維信兄、年初甫退休的錦郁姐,以及美術中心的泰裕主任和「一大群」優秀的、和副刊並肩作戰的美術編輯們。我經常掛在嘴邊說,能在副刊工作是被祝福的,而能跟這一群朋友一塊兒工作,我被祝福得最多!當然更感謝領我入門的義芝大哥、煥彰大哥、新彬姐、偉貞姐,指導我許多事。還有瘂公、作老,每次見面都為我打氣。不斷為我打氣的朋友太多太多了,無法一一寫在這裡,但每一句鼓勵我都存放心中,喔,批評也是的。還有,本來提工作上的長官,似有諂媚之嫌,但這本書意義不同,我一定要在這裡說:在紙業媒體如此艱困的時局裡,聯合報,以及我所有共事過的長官們,仍然給予副刊這樣大的空間,這樣自由的發展與尊重,我深深感謝!
這本書獻給所有喜愛副刊的人。
看更多
詳細資料
ISBN:9789869416856
叢書系列:看世界的方法
規格:平裝 / 224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部份全彩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本書分類:文學小說> 華文創作> 散文
本書分類:社會科學> 閱讀
· · · · · · (
收起)

 名為我之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名為我之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文藝春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文藝春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臺北女生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臺北女生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鹽田兒女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鹽田兒女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她們都是我的,前女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獸身譚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獸身譚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有型的豬小姐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有型的豬小姐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御身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御身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三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第三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丁玲名作欣赏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丁玲名作欣赏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ぼくは明日、昨日のきみとデートす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ぼくは明日、昨日のきみとデートする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博士熱愛的算式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博士熱愛的算式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一生中的一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一生中的一天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一百擊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一百擊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濕地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濕地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有间汤药铺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有间汤药铺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中国画名家经典画库.现代部分.张大千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中国画名家经典画库.现代部分.张大千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Rome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Rome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海街diary すずちゃんの海街レシピ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海街diary すずちゃんの海街レシピ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冰冷的甜蜜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冰冷的甜蜜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