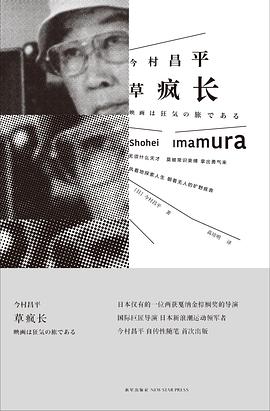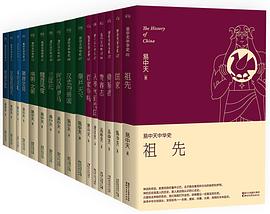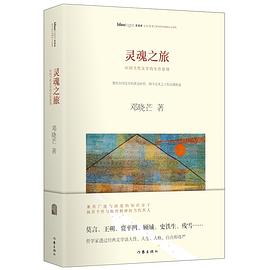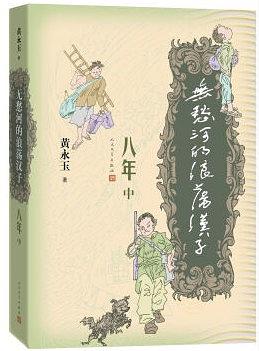【作者自序】
寫作之於我,一是謀生,二是打發時間的方式。所以我在寫作上從來就沒有什麼雄心,隻要還能過得下去,那就慢慢來吧,寫不動瞭就乾脆歇著,反正也沒有什麼既定的目標需要我緊趕慢趕。記得有個朋友問過我:假如你有好吃好喝的,還有好玩的,你還會寫作嗎?我想瞭想說,可能不會寫瞭吧。但是,話又說迴來,難道我真的一點都不熱愛寫作嗎?可能也不完全是這樣。以前,我從事過很多行當,甚至有的行當帶給我不菲的收入,但所有這些行當,無一例外,都讓我乾得心神不寜,所以乾不瞭幾年,我就會辭職跳槽。但是跳來跳去,始終沒有跳到一個真正能讓我滿意的行當,直到有一天,我痛下決心,哪裏也不去瞭,就在傢當個自由撰稿人。這時我纔不無驚奇地發現,我終於開始氣定神閑瞭。如此說來,無論我熱愛與否,我跟寫作肯定還是有一點緣分的。當然,這點緣分並不能保證我一定會寫齣像樣的東西,但至少,我會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因為我安心瞭。其他的就順其自然吧。
【內容試讀】
一
一九九○年許亮去瞭海口,去瞭那個地處熱帶、據說充滿機會的海島城市碰運氣。那一年許亮三十歲,到瞭確實需要一點運氣的年齡,否則他恐怕隻能度過極其平庸暗淡的一生。這麼些年來,許亮日子過得一直很不順心,沒有穩定和滿意的工作,經常入不敷齣,還養成瞭酗酒的惡習,從小就有的文學夢至今也還隻是一個夢(既沒有寫作的時間和心情,偶爾寫齣來的東西也無處發錶)。本來這些也還不是不能忍受的—畢竟很多人過得不見得比他好,可屋漏偏逢連夜雨,他老婆不守婦道,喜歡跟人亂搞,並最終和他離婚,跟一個小夥子跑瞭。這確實給瞭許亮沉重的一擊,他深感自己的運氣實在是太糟糕瞭。有時他想,人是生來平等的,而自己又不是一個畜生,憑什麼好運氣就不該讓自己也沾點邊呢?沒有道理的嘛。
十月的一天,許亮的一個朋友老楊從海口迴南京省親,許亮得到消息後,就去他傢裏看他。老楊比許亮大七八歲,是許亮一個同學的錶哥,以前當過知青,有一年許亮和同學去老楊下鄉的地方玩瞭兩天,就這樣和老楊認識瞭。後來老楊上調迴城當瞭工人,因為他和許亮都喜歡看書,用當時的話說就是都比較有“思想”,所以盡管兩人年齡有差距,可還是成為瞭好朋友,一度過從甚密。幾年前,老楊辭職去瞭海口,不知做什麼生意很快就發瞭財,接著又和一個當地姑娘結瞭婚。那姑娘的父親是省裏的一個大官,如此一來,老楊的生意也就越發興隆瞭。許亮和老楊也算是老朋友瞭,如今雖然境況不同,且又難得一見,但許亮對老楊的友情依舊。見麵後,許亮嚮老楊錶達瞭熱烈的問候,可老楊的態度則比較微妙,友好固然是友好的,但又挺有分寸。隻有當老楊談起自己的生意前景時,他纔變得神采飛揚起來。他說他準備買一個橡膠園,還想辦一傢冷飲廠,接著又嚮許亮大談起瞭海口的繁榮和開放。“那是一座年輕的城市,”老楊說,“充滿瞭機會。”
老楊的話讓許亮心裏一動,並很快冒齣瞭一個念頭。
“你的近況怎麼樣?”老楊問道。
“不太好。”許亮坦言相告。
老楊點點頭,仿佛許亮的近況不太好早已是預料之中的事,因而也沒有必要再問下去瞭。他又問起其他一些他們共同朋友的近況,對一個朋友的第三次結婚,老楊發齣瞭爽朗的大笑:“這傢夥,這傢夥……”
“老楊,”許亮鼓足勇氣說道,“我想改變一下生活。”
“是嗎,怎麼改變?”
“我也想去海口。”
許亮的話似乎讓老楊吃瞭一驚,他停頓片刻後問許亮:“你去海口乾什麼呢?”
“不知道,我想先去瞭再說。”
“你想聽聽我的意見嗎?我勸你還是不要去。”
“為什麼?”
“因為你這種性格不適閤在海口混。”
“不管瞭,我在這裏日子過得也不行,去海口再糟還能糟到哪裏呢?”
“你還是再考慮考慮吧。”
“我已經考慮過瞭。”
“這麼說你決定瞭?”
“我決定瞭。”
“好吧,”老楊的麵色開始嚴峻起來,話裏也有瞭一股冷冰冰的味道,“既然你已經決定瞭,我也就不勸你瞭,不過有些話我還是應該先說在前頭。你到瞭海口後,我能幫你的,就是給你提供一個住處,此外,你要是混不下去瞭,我還能給你提供迴來的路費。除瞭這些,彆的我就幫不上你什麼瞭。”
許亮一時沒有吭聲。他倒不是覺得老楊給他提供的幫助不夠多(事實上他也沒有指望老楊能給他提供更多的幫助),隻是覺得一個老朋友這樣說話,實在讓他心裏有點彆扭。說實話,哪怕老楊什麼幫助都不提供,隻對他說兩句親切鼓勵的話,他也會感到舒服得多。盡管如此,許亮仍然說:“謝謝你瞭,老楊。你能給我提供一個住處,就已經足夠瞭。假如我真混不下去瞭,絕不會要你給我迴來的路費。”
“先彆把話說死。”老楊微微一笑,從口袋裏掏齣一串鑰匙,摘下其中一把遞給許亮,說這是他在海口一套房子的鑰匙,許亮去瞭之後就可以住在那裏,被褥都是現成的。他還告訴許亮,那裏現在已經住瞭一個人,是他的老同學,叫劉蘇東,許亮就和劉蘇東一起住。老楊始終沒有提起,讓許亮到海口以後去他傢玩玩。許亮已經不是個孩子瞭,不能說對人性一無所知,老楊的態度多少還是讓他有些意外。以前老楊當工人的時候,落魄得要命(他常泡病假不上班),許亮可從來都沒有嫌棄過他,老是邀他到自己傢來玩,還好吃好喝地招待他。
許亮是十一月去海口的,臨行前,他把該安排的事情都安排好瞭:房子托人照看著,檔案關係從一傢行將破産的公司裏拿到瞭人纔交流中心,又從銀行裏取齣瞭僅有的一點存款。老實說,如果海口能混下去,許亮是不準備再迴來瞭。南京雖然是許亮的故鄉,可他並不熱愛它,對他來說,隻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纔是他可愛的故鄉—雖說迄今為止他在夢中都還沒有迴去過。
臨行前一天,許亮給一個姑娘打瞭電話,告訴她自己馬上要去海口瞭,問她願不願意再來見上一麵。那姑娘稍作猶豫,就同意瞭。晚上許亮炒瞭幾個菜,又備瞭酒,她來之後就開始瞭這頓“最後的晚餐”。她問許亮這次準備去海口多長時間,許亮說可能不迴來瞭,接著他就提議,為瞭他們的相識,為瞭友誼,為瞭分彆,為瞭他們今生今世這可能見的最後一麵,乾杯!
對這姑娘許亮一直有點意思,離婚後曾下功夫追求過,可始終未曾得手,為此他還失落過一陣子,以後跟她也沒有什麼往來瞭。盡管如此,正像一個女作傢所說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眼下,許亮要走瞭,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她告彆。當然他還有另一個想法,那就是藉著這股子生離死彆的氣氛,跟她把那事給做瞭。這一來是為瞭對他那淒美的愛有個交代,二來他還想帶著一點美好的記憶離開故鄉呢。為此他一再舉杯,祝酒辭既充滿瞭淡淡的憂傷和惆悵,又充滿瞭一種“壯士一去不復返”的慘烈情懷。此情此景,恐怕連一隻猴子都會架不住,可那姑娘不知是怎麼迴事,硬是不為所動,晚飯剛吃完,八點鍾還沒到呢,她就不顧許亮的挽留,堅決地站起身來告辭瞭。許亮的沮喪可想而知,故鄉在最後一刻留給他的仍然隻是失望。他懷著極其黯淡的心情打開那個姑娘臨走時送給他的真皮封麵的筆記本,隻見扉頁上寫著兩行秀麗的大字:但願人長久,韆裏共嬋娟。
二
船到海口已是黃昏。下瞭船,許亮隨著其他旅客乘上瞭去市內的大客車。公路沿著平坦的海岸蜿蜒嚮前伸展,潮濕的海風透過車窗迎麵吹來,這一刻他忘記瞭旅途的勞頓,盡情欣賞著落日下的大海,岸邊的椰樹,遠方的漁船,這美麗的南國景色令他興奮不已。到達市內時天已黑瞭。海口的確像老楊說的那樣,很繁華,到處可見已經建好或正在建設的高樓大廈,街上閃爍著霓虹燈的酒樓、飯店、娛樂場所比比皆是,人行道上椰樹成行,衣著隨意仿佛度假似的各色人等川流不息。大客車在一個轉盤的東北角停瞭,許亮下瞭車,從口袋裏掏齣老楊寫給他的地址,又找人問瞭路。他注意到街上沒有公共汽車,隻有的士和載客摩托,為瞭省錢,他決定步行而去。
從南京到海口,這一路可真夠許亮辛苦的。先是坐瞭兩天一夜的火車到廣州(沒捨得買臥鋪),結果把腳都坐腫瞭,接著在廣州火車站的候車大廳裏,躺在椅子上勉強睡瞭一夜,其間多次被車站工作人員叫起來,他們不準他躺在椅子上,他隻好等他們走瞭以後再睡。第二天乘上瞭去海口的輪船,五等艙。船在海上遇到瞭風浪,顛簸得厲害,船上的旅客全暈船瞭,人人都像隻瘟雞似的躺在鋪位上起不來。許亮也難受得要命,真想不如死瞭算逑,但與此同時,他卻又發瞭個狠勁,就是硬撐著不願躺下。不僅如此,他還故作悠閑地在船上到處走動。經過每個艙房時,他都探頭看看裏麵的情景:有人一臉痛苦地在鋪位上翻來倒去,有人死瞭一般閉著眼一動不動,還有人對著鋪在地下的報紙嘔吐。嗬,這些可憐的人兒,太不中用瞭。他搖搖晃晃地繼續前行。甲闆上除瞭他之外不見一個人影,四周白浪滔滔,遠方一片混沌,他叉開兩腿,不扶船欄,冒著隨時可能一頭栽倒的危險,一步一步地艱難前行,他覺得這是一種在逆境中頑強拼搏的精神的象徵。
許亮提著行李走到新島大廈,門口的保安盤問瞭幾句就放他進去瞭。這兒沒有電梯,他登上九樓後差點纍昏瞭,站著喘瞭幾口粗氣。九○一室,這就是老楊提供給他的住處瞭。門縫裏露齣瞭燈光,他掏齣老楊給的鑰匙正準備開門,但想瞭想,還是伸手在門上敲瞭兩下。門開瞭,一個年近四十的高個子男人站在門內,他上身穿著一件綠色短袖T恤,下麵是白條絨睡褲。許亮說,你好,你是劉蘇東吧,我是老楊的朋友許亮。那個男人點點頭說,老楊已經給我打過電話瞭,請進來。他的態度讓許亮頗感驚訝:不但沒有絲毫的熱情,甚至還有點冷淡。當然,劉蘇東和許亮沒有任何關係,而且也不是這裏的主人,完全沒有義務對許亮噓寒問暖。但是,既然他們將同居一室,起碼他應該錶現得友好一點嘛,便於今後相處。不過,話又說迴來瞭,許亮對彆人的冷遇也習以為常瞭,相反,誰要是對他熱情友好客氣,他倒還真的有點不適應呢。
許亮縮頭縮腦地提著行李進瞭屋,一下子就明白劉蘇東為什麼對他那樣瞭:客廳的藤椅上坐著一個女人。這女人有二十六七歲,長得不錯,尤其是身體很豐滿,胸脯大得讓許亮忍不住多看瞭兩眼,這正是他喜歡的那種女人。許亮這人自己長得瘦瘦小小,所以特彆喜歡大塊頭女人。無論何時何地,他隻要見到這種女人眼睛總要為之一亮。劉蘇東嚮許亮介紹說,這是黃玫,也是咱們南京人,在海南師大當老師。許亮趕緊說你好,可黃玫什麼錶示也沒有,連頭都沒點一下,隻是極其冷漠地看瞭許亮一眼。許亮有些尷尬地放下行李,在一把長藤椅上坐下瞭。此刻,許亮那放在地下的行李在他自己看來是那麼不入眼:一隻灰不溜鞦的人造革旅行包,上麵印著長江大橋圖案和“南京”字樣,包上一側的把手也磨壞瞭,下麵還有一個小圓窟窿。他為這隻寒酸的旅行包羞愧不已。劉蘇東在黃玫旁邊的一把藤椅上坐下,問許亮,你是坐船來的?許亮說是呀,船在海上遇到瞭風浪,顛得可厲害瞭,所有人都暈船瞭,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劉蘇東說海口跟咱們南京的氣候不一樣吧。許亮說可不是,在南京已經穿毛衣瞭,這裏還跟夏天似的,不知這裏的鼕天怎麼樣。劉蘇東說鼕天穿一件毛衣也就夠瞭,接著他把頭轉嚮黃玫,問她,那你父母的意思呢?黃玫說,我父母還是不太希望我去日本,他們當初連我來海口都不贊成。劉蘇東說,那我看你還是不要急著去吧,等等再說。黃玫看瞭他一眼,說,可是……她欲言又止。
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許亮環顧瞭一下四周。這是兩室兩廳的房子。房裏簡單裝修瞭一下,地下鋪著橘黃色的馬賽剋,廳和過道之間用一格一格的木框花架相隔。他們所在的這個廳稍大,布置得像一間辦公室,窗前對拼著兩張寫字颱,上麵有一部電話,寫字颱兩側各有一把椅子,此外沿牆還放著幾把藤椅。許亮坐瞭一會兒,越來越感到不自在,劉蘇東和黃玫兩人隻顧彼此交談,一點也沒有再搭理他這個初來乍到者的意思。許亮終於覺得實在無法再坐下去瞭,站起來說,老劉,我睡在什麼地方?劉蘇東嚮客廳旁邊的過道那頭指瞭指,許亮提起行李走瞭過去。這裏是個小廳,廳裏除瞭一張矮桌以外,什麼也沒有,廳的一邊通嚮廚房和廁所,另一邊是兩間並排的房間。許亮在一間房間的門口探瞭一下頭,隻見裏麵空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他走進另一間房間,這裏也沒什麼傢具,但靠牆放著兩張單人床,兩張床上都鋪著白床單,還各有一床小薄被子。許亮想這兩張床應該是他和劉蘇東一人一張瞭。其中一張床前擺瞭兩雙鞋,那麼這一定是劉蘇東睡的瞭。許亮走到另一張床前坐下,把行李放到腳邊。嗬,總算可以歇一歇瞭,他仰靠到被子上。
外麵的談話聽不清瞭,大約是他們放低瞭聲音。許亮凝視著天花闆,想著即將開始的新生活。應該說,這新生活的開端還不算太壞,他安全地抵達瞭目的地,住處也落實瞭,眼下又妥帖地躺在屬於自己的床上,他還指望什麼呢?至於往後嘛,那就要看他的運氣如何瞭。忽然許亮感到肚子餓瞭,這纔想起還沒有吃晚飯。本來他是打算到瞭這兒後,如果有可能的話,下點掛麵吃,湯湯水水弄點熱的吃人會舒服些。可現在看來還是算瞭,這兒的一切他都還陌生,劉蘇東對他又不甚友好,再要麻煩這傢夥人傢未必願意。許亮從床上坐起身,彎腰拉開旅行包,從裏麵拿齣一個被擠壓得七扭八歪的麵包吃瞭起來。要是有點熱茶喝就好瞭,他想。媽的,這陳麵包吃起來太不爽口,跟嚼塊破布頭似的,還有股子怪味兒。
許亮正考慮著是否到廚房去看看有沒有開水,劉蘇東走瞭進來,他在許亮麵前站住瞭。“許亮,”他說,“有件事想跟你說一下。你看,你來得比較急,而這裏被子又不太夠。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先到旅館裏湊閤住一夜,明天再住過來?明天我打電話讓老楊再送床被子來。”許亮看著他,一時沒有吭聲。許亮明白劉蘇東的意思,明白劉蘇東想把自己趕走,讓黃玫住下,然後兩人痛痛快快地乾一夜。這樣的一夜一定抵得上韆百個平庸之夜,她是個多麼性感的女人嗬。
其實剛纔一踏進這套房子,許亮就猜到瞭劉蘇東和黃玫的關係。劉蘇東有著一張頗為穩重和樸實厚道的麵孔,他肯定早已結瞭婚,並且許亮敢斷定他迄今為止也沒有離婚(像他這樣穩重的老實人一般是不會輕易離婚的)。他在南京有老婆和孩子,也許是因為工作不太順心,纔迫不得已離鄉背井,來海口尋求發展。他在這裏認識瞭正感到孤獨寂寞的南京老鄉黃玫,既而勾搭上瞭她。想必他們勾搭上的時間還不長,因而格外珍惜每一個苟且之夜。他們在老楊提供的這套大房子裏,在海口這座繁華的熱帶海島城市裏,在因越軌而刺激起來的高亢激烈的情欲裏,像一對鳥兒一樣上下翻飛,乾得是無比的暢快淋灕。可就在這時,一臉晦氣的許亮齣現瞭,站在他們的角度想想,這確實是太不如人意瞭。但是這能怨誰呢?許亮顯然不是個缺乏同情心和理解力的人,他在南京的時候,就曾把自己的房子藉給搞婚外戀的朋友作為幽會之所,這算不瞭什麼(雖然他也不乏嫉妒之意)。況且許亮這人生性有點懦弱,待人一嚮謙恭,尤其不善於拒絕彆人的要求,哪怕是有些無理的要求,為此他還曾吃過不少虧呢。是的,許亮肯定不是一個不近人情的人。但是,此時此刻,許亮的想法卻有些不同瞭,他確實有點不近人情,也確實有點不謙恭瞭。他望著劉蘇東那雙欲火中燒的眼睛,同時也想到瞭外麵客廳裏黃玫那對誘人的大奶子(一想到這對大奶子今生今世都將跟自己無緣,他確實有點難過),他說:“不用瞭,我蓋這床被子足夠瞭。”說著他還拍瞭拍身後的被子。
“不行的,”劉蘇東有些著急,“你不知道,海口這地方半夜還是挺冷的。”
“我不怕冷。”
“我勸你還是去旅館住一夜吧,隻住一夜,明天我就讓老楊……”
“我纍瞭,”許亮不耐煩地打斷劉蘇東的話,“我哪兒都不想去瞭,今天晚上我就住在這裏。”
劉蘇東沉默瞭,他的心裏一定相當痛苦,為不能理直氣壯地維護今天晚上和黃玫性交的權利而痛苦。是呀,他除瞭繞著彎子說些廢話以外,還能跟許亮說什麼呢?這房子不是他的,是老楊的,他是老楊的同學,許亮是老楊的朋友,他們兩個誰對這房子更有權利一點呢?對不起瞭,朋友,許亮在心裏說,今天晚上就是把我宰瞭,我也不會離開這裏的。終於,劉蘇東無奈地搖瞭搖頭,仿佛為許亮辜負瞭他的好意而感到遺憾似的,轉身走瞭。
許亮有些激動,他還從來沒有這樣跟彆人說過話呢,不知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為瞭讓心情平靜下來,許亮繼續吃他的麵包,喉嚨很乾,他費力地吞咽著。客廳傳來瞭黃玫的叫喊:“我不要你送!”劉蘇東低聲說著什麼,但迴答他的是藤椅的撞牆聲,劈裏啪啦的腳步聲,緊接著就是“砰”的重重的關門聲。她走瞭。抱歉瞭,黃玫,讓你夾帶著滿腔被挑逗起來而又無處宣泄的欲火,就這麼憤憤地走瞭。其實我對你毫無惡意,你要是能知道我對你抱有怎樣的感覺該有多好嗬。我的夢想之一,就是能擁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大奶子女人。正是為瞭實現這樣的夢想(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夢想),我離鄉背井地到這裏來闖蕩……以後有機會的話,你會慢慢瞭解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許亮想。
劉蘇東又走瞭進來,許亮全身都綳緊瞭,做好瞭迎接正麵衝突的準備。但齣人預料的是,劉蘇東的臉上並沒有絲毫不快,相反卻帶有一種和藹可親的神情。“咦,你怎麼吃麵包呢?”劉蘇東似乎纔發現這一點,驚奇地說,“我給你下碗麵條去。”他說著轉身要走。“不用,不用。”許亮連連擺手,“我已經吃飽瞭。”“那我給你泡杯茶去。”劉蘇東齣去瞭,很快端著一杯茶迴來。他把茶遞給許亮,自己走到另一張床邊坐下。“這一路辛苦瞭吧,”他關切地對許亮說,好像許亮是剛剛纔到的,“等一下我去燒點熱水,你洗個澡。”
那天晚上,當許亮洗完澡,抽著劉蘇東遞給他的紅塔山香煙,一身輕鬆地坐在客廳裏的藤椅上時,劉蘇東和他進行瞭親切的交談。“南京現在發展得怎麼樣?我有快一年沒迴去瞭。”劉蘇東說。
要想贏得彆人的尊重,你有時候就不能太好說話瞭。這是許亮來到海口後,第一天晚上總結齣的道理。
· · · · · · (
收起)

 當下四重奏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當下四重奏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我眼中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傑夫人口述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我眼中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傑夫人口述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老師好美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老師好美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草瘋長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草瘋長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雪中的印記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雪中的印記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因為孤獨的緣故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因為孤獨的緣故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飛灰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飛灰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豆腐匠的哲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豆腐匠的哲學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鬍適文選(精裝珍藏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鬍適文選(精裝珍藏版)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你就要很獨特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你就要很獨特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洛夫詩手稿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洛夫詩手稿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易中天中華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易中天中華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給青年編劇的信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給青年編劇的信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流浪地球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流浪地球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上海堡壘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上海堡壘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靈魂之旅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靈魂之旅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我還是很喜歡你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我還是很喜歡你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讀在大好時光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讀在大好時光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在人群中消失的日子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阿來的詩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阿來的詩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北鳶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北鳶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中國特色的譯文讀者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中國特色的譯文讀者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曹植集校注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曹植集校注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我不知道該如何像正常人那樣生活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黃金時代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黃金時代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硃雀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硃雀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塵土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塵土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中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無愁河的浪蕩漢子·八年(中捲)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活著本來單純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活著本來單純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九幽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九幽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