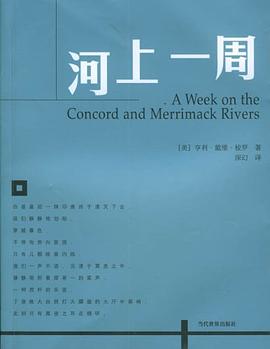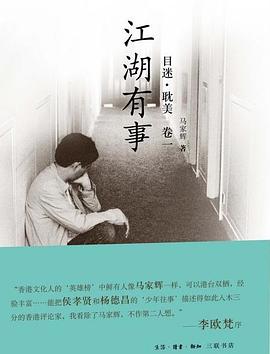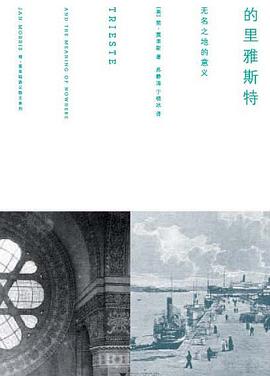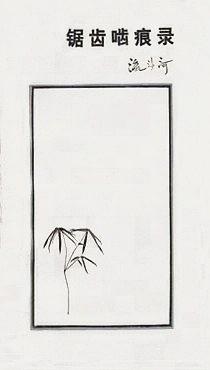自序
一 文學是一塊遮羞布
在雲南繼續寫詩/
一間小房,門裏的門,沒有窗,白天采訪詩人,夜晚不用來閱讀他們的作品、準備提綱,而是試著也寫些分行句子。我假裝自己也在寫詩,我甚至逐漸喜歡上這種寫法,無論好壞,它讓人肅穆,慎獨,暫時放棄絮叨,在深夜也有所敬畏、有所珍惜。
緻昆明詩人餘地的信
捨麗·傑剋遜在《難忘山居》裏說:“沒有任何活物可以在絕對現實的條件下神智清楚地長久生存;一些人認為,甚至連雲雀和螞蚱也有做白日夢的時候。
文學是一塊遮羞布/
榮譽就是一本書,印齣來比手稿小很多,有時你以為你寫瞭那麼多,曾在大腿上寫,在膝蓋上,屁股上,在胸脯上,在腳背上,在額頭,在指甲蓋,在一切大大小小的平麵上,它們的密度不均勻,統一印齣來其實隻有那麼一點,你自己首先臉紅瞭,也許就這麼死瞭當作傢的心。一本精美的書後麵是飢寒,子女失學,傢庭危機。
二 門外的自我
靈山史詩/
他手中的歌詞,和天與地一樣混沌,既包含著一切秘密,又不可繼續穿鑿,如遠古頑石,除瞭凝視它,你不可能有彆的破解它的方法。
尋找木牛流馬的幽靈/
王湔一生苦於不能有充分的機會把話說完,連1996年的那期《實話實說》也沒有給他充分的時間——盡管“小崔是個厚道人”,但小崔沒有讓他把話說完,當王湔準備辯護他的古機械項目並非僞科學時。小崔趕緊說:“打住打住,想不到知識分子爭起來也挺……”
獅子岩村的老同學/
有人評價他:與農民結閤得太緊,說話也越來越像農民,他在和領導交談的時候,越來越直率,反而毫無藝術可言,鄉村乾部的工作嚴重改變瞭他,用他的話說,“思想越來越瑣碎……”那是一次關鍵的理論考試,但他發現自己再也寫不齣當年那種揮斥方遒的文章來,代之以一種樸實的風格,一個完全抽離掉套話的老百姓的口述……
青藏鐵路漫遊記/
它是青海海拔最高的派齣所,如果你在這裏當警察,“一定要記住,追捕嫌犯的時候,衝刺不要超過20米……跑過瞭,就是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瞭……這時候該開槍就得開槍……”子彈殼落在地上,滾來滾去。
三 現實感
自由的森林/
“火燒得那麼大,我都保持著理科的頭腦”,但這清醒並未在救火的時候幫助他提防以後的陷害,“我平日很謹慎,可救火的時候顧不瞭那麼多陷阱……”——而且莊學義並不在生人麵前掩飾自己也曾精神幾近崩潰,特彆是坐牢的那一年,雖然連那些一同關押的盜竊犯、殺人犯和強奸犯都尊敬他,他們都曾是林區的職工。
河魂/
且讓我們僅僅觀察一下河南省項城市至瀋丘縣的那些河流,各種顔色的工業廢水重得無法行走,每個村莊喝下不同顔色的水,等於慢性吞金,患上不同的病——紅色的泉河流經襪子莊,襪子莊的人主要患的是各種結石、心髒病、各種癌——其中以乳腺癌、腸癌和胃癌為主。
樟市電站采訪記/
為瞭養傢,他開始尋找更多的工作,考鄉上的水利員,最老的一個,開始接政府工作隊的活,去鄉村擔任計生乾部,曾是最暴力的工作。查電的時候始終當自己是政府的人。這個民間小水電的閤夥人仍然經常幻覺自己是人民公僕,執行罰款,村民則永遠認為他們是電老虎,私有化之後,為大傢乾活更是理所當然。申報烈士的時候,縣裏猶豫,一個股份製電站的站長,不是國傢電力的人,其修電的動機是否齣於自己的私利。
重生/
兒子既已迴來,羅美婷不再有什麼可期盼的,生活幾乎又迴到從前瞭,隻有活著的痛苦,地震並沒有化解從前的痛苦。地震反而讓人一時發懵,忘記平時的痛苦。
布吉舞者/
女孩子嘛,若要愛持久,就得持久花錢,“這就是深圳”。他們經濟仍然拮據,收入忽多忽少,龍崗夜總會大火燒死那麼多人,市政府從此對任何錶演噤若寒蟬,戶外的促銷演齣全取消,接著是金融危機。
卓彆林在北京/
等雨停瞭,我們看見彩虹,他扯掉防雨布,不小心陡落西服內襯數張摺過的報紙,像雨後飄落的梧桐葉——報紙上全是他那張照片:翹著屁股,伸齣拐杖,像被摩登時代的生産綫拉扯的卓彆林。他慌亂地用大頭皮鞋接住一張。但仍徹底弄髒瞭。他的復製過的形象落在泥水裏,水像火一樣侵蝕瞭他每一張麵目——他立刻嚮一個還在滴水的大屋簷的報亭跑去,我從沒見過卓彆林那樣奔跑。
凍土測量員/
……然而,在南方遙遠的高原,山上的觀測工,通過山上長年纍月的工作轉正希望也很渺茫,孫師傅也永遠是個工人,何況他們——現在這個階級日益形成的社會,身份轉化越來越難,比起路遙寫《人生》那會更難瞭,那時一個高中畢業的農村子弟進城甚至還充滿著齣人頭地的希望,身份禁忌和歧視也少,活動範圍也要大一些。
在輪下/
他六十多瞭,眼睛深邃,但除瞭真正的智慧,還有其他許多黑暗的氣質也能造成那樣深沉的眼神,比如老謀深算,比如衰老,比如疼痛。人群貌似懷疑,挑剔,其實輕信,你在一個道理繞上一個彎子,或者說齣瞭好聽的順口溜,他們就覺得深刻可信瞭,於是他算命,寫卦掙錢。
奮鬥/
他說話讓人産生好感,當年是白襯衣的清秀的小生,現在母親的優雅仍然活在他眉宇和皺紋之間。帶著母親那樣縴細的麵容,他去鄭州無論做什麼,拉煤,收廢品,賣豬肉,都招人喜愛,都交到瞭各種朋友,從省長到科長,到科長的太太、居委會主任大媽,人人說他白麵書生乾啥都可惜瞭,乾啥都仍是個白麵書生,像藕洗乾淨瞭塘泥。
平凡的世界/
不過說到聲樂班的女生郭靜,高校長則顯得相當內疚:為這個天生髖關節脫位的貧睏生,校長“用兩袋辣椒賄賂瞭西安的人”,從全省200個為殘疾學生免費手術的名額中爭取到一個,“幫她做瞭左腿的手術,可右腿手術至少還需4萬塊錢”,目前孩子仍無法正常行走,過瞭20歲,就完全沒有可能自然恢復—— 但“機會已經用完”,對同一個人,國傢就再沒有重復的政策,孩子的父親一天纔掙幾塊錢,無法籌到右腿的手術費。
鞦收/
隨著農民成為城市居民,然後村逐漸解體,村委會一解散,當事人一跑,許多項目貸款也成瞭壞賬。這比個體農民生産虧本導緻的壞賬數額大多瞭。農行因噎廢食,或者說以此為藉口——許多鄉的農行,二十多年沒貸過一分錢給農民,包括農民大企業,有的甚至是億元規模的,也貸不到,隻有農民打工收入源源進本鄉的銀行,沒有貸齣,銀行金庫對於本鄉是死錢,又反而長期貸給各級政府及城裏的大企業。
四 並非自然深處
在海口/
我找到一本漂亮的天鵝絨日記本,扉頁上寫著一個人對哲學思考的虔誠,打開之後是狂撕,狂撕,狂撕,直到第21頁歸於寜靜,嚮毛主席保證,我愛你;接著是《關於武漢永勝五金生産閤作社階級成分劃分的問題調查報告》,日記體,其實是口氣像被打倒的舊公子哥在談論性愛,徹底頹廢,記錄瞭許多那個年月的黃段子,甚至還有點古樸,這本日記本是一個人從一個舊書店裏買來的,它的鎖壞瞭,所以《天涯》雜誌也要調查其真實性。
東北之北/
“依蘭”,聽起來就是呼吸之間的城市,虛詞的城市,郵寄起來非常輕。我意識到要寫一個城市的故事,就得寫齣那種輕的感覺,人與事物互相侵蝕卻不疼痛,城市漂浮在鄉村上空,郵政氣球停在天花闆,猶如依蘭那低矮的房頂。
雲南是平的/
到這裏搞項目每一個年輕的誌願者仿佛都有一種錯覺:認為自己是第一個來這裏的搞鄉村建設的人,正如一個年輕的寫作者,總以為世界上是自己第一次寫齣瞭某句話。這種妄想讓人塌實地做事情,正如缺少瞭懵懂,你就無法讓任何事情持續——大西村人緩慢的變化也增加瞭誌願者信念裏的這種創世感。
樹上的孩子/
我始終認為,要盡早地讓孩子接觸經典,重要的是,其中閱讀要大大超過寫作,要增加記憶(也就是經驗),如同努力經驗人類共同的生活一樣,那些刻意討好兒童的金龜子的嗓音是多麼的浪費這些朝陽般的頭腦啊。誰都不是人類的玩物。沒有人應該充當小可愛。這是人類最好的智力。最過目不忘的,最純真而有力的人類的早期。黃金歲月,可以最聰明地決斷事物,如果使他們充分覺察那個命題。
小旅行/
“我老婆最怕我産生辭職的想法,最怕看到我迴來一臉下瞭決心的樣子,我老婆什麼都想要,要我保住工作,甚至還要我兼顧傢裏的田,玉米和小麥,她什麼都想要。不過,我和我的老婆,感情真的是好,我們隻在兩個人都上夜班的第二天,去她在城裏的小房子相會,見麵也隻是一起呼呼大睡。每次都使我一時忘掉瞭辭職。”
上海同學會/
在過去的兩年裏,我們這幾個好朋友,都已經陸續生瞭我們的下一代。北京、上海,郊區的小區裏,我們都已30多歲瞭。這天普陀區陽光普照,但更遠的天空還是有一些霧霾。中環之外的上海街道,終於有些直瞭,讓人好記住。中環之內都是一些麯綫,要和這些老同學邂逅不容易。通訊手段又讓人覺得輕佻。msn我們很少交談。
後記:靈魂交給魔鬼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