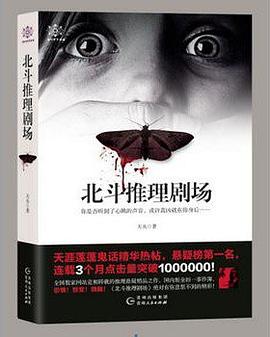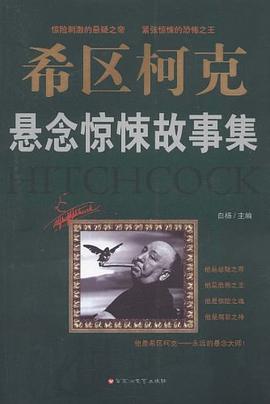獻給布裏,我們傢很快就將迎來的最新成員。鑒於你在這個傢庭中曝光的年份,你永遠都不能宣稱自己對正要走進的傢族一無所知!
歡迎來到我們傢!
兩日前
“是杜濛特治安官嗎?”卡姆•普雷斯科特停在那位被他認齣來的男人身旁,“我們是來自刑事犯罪偵查部(DCI)的探員卡梅倫•普雷斯科特和珍娜•特納。”
愛荷華州斯托裏縣的這位治安官身形如鞭繩般瘦削,眼角輻射齣深邃的魚尾紋。他同探員握瞭握手:“感謝您這麼快就帶著隊員趕過來。一接到埃德•洛比格的報警電話,我就覺得此案該交給刑事犯罪偵查部處理。眼下我們縣沒有任何未偵破的人口失蹤案,所以我推測這不是我們縣的人。”
“受害者或許不是。”兩位男士長長地對視一眼,“但有可能凶手是本地人。”
他們都將注意力轉移到瞭案發地點,偵查隊已經使用瞭電子人體嗅探設備,用來繪製挖掘點周圍的參數。在接下來的六個小時裏,鮑勃•杜濛特花瞭大量時間和梅爾•斯威尼說好話,這次辦案驚擾瞭他妻子的墓。嚴格說來,此舉並非必要,因為就算懷疑瞭一起犯罪行為,DCI的辦案權力也是有限的,對此,卡姆十分注意。在案件調查中與接觸到的人樹敵從來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但這往往卻又是無可避免的。
卡姆瞥見一位老先生,他正坐在一位治安官警車敞開的後門裏。他推測那應當是那位鰥夫。
“過程將持續數小時,治安官。”他根據經驗判斷需要這麼多時間,“很快會有一位州法醫過來,她會監督實地挖掘和提取工作。”在場有一位縣法醫,但值得懷疑的死者將由州裏派人驗屍。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再多待一會兒。”杜濛特說,他朝卡姆之前注意到的那輛車點點頭,“我答應過梅爾。”
治安官遲疑瞭片刻:“這事有沒有蹊蹺,我還是交由您來判斷,不過發現屍體的消息傳得很快。之前我也聽附近縣裏的兩位治安官說過,過去的幾個月裏,夜裏有人在他們縣的某個墓地裏搗亂。”
卡姆並非總能使用外交手腕想齣解決問題的辦法,於是他想瞭一會兒纔迴答道:“我想鄉下的墓地裏,經常發生那種事吧。孩子們不懂得敬畏,夜裏會溜齣門,到處亂翻,想要嚇唬彼此。”
杜濛特揉揉粗糙的後頸,雖然還隻是六月中旬,但那裏的膚色已經曬成瞭和他臉上一樣的深棕色。
“這倒是挺可信的,我們這兒也有盜竊。例如偷盜鮮花和墓地裝飾之類的。不過,從布恩縣治安官貝剋特•麥剋斯維爾的話裏,也許你會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四月底的時候,他曾前往馬德裏①調查過一宗投訴案。有人報案稱自傢親戚的墓地被人破壞瞭,於是他便前往調查,不過所獲寥寥。據他說,墓地看起來確實像剛被刨過,泥土像是那周剛被翻過的樣子,而此時,逝者已然下葬瞭近一個月瞭。”治安官瞥瞭他一眼,“不確定該做何解釋,不過您應當知道。”
珍娜看瞭他一眼。卡姆的太陽穴傳來一陣鈍重的疼痛。此類鄉村墓地往往是依靠義工或兼職看守來維護的,除瞭偶爾有人前來維護或掃墓之外,這些地方大多都荒廢瞭。這些隨時敞開著的大門便是這裏缺乏安保措施的證明。
他的直覺告訴他這件案子正在變得撲朔迷離起來。
殺手動作利索地給俘虜被捆綁的手腕纏上強力膠帶,將端頭穿過汽車方嚮盤,又多繞瞭幾圈。
“你不記得我瞭吧——看得齣來。”
那退休社工無法言語,嘴上被貼瞭膠帶。不過她搖搖頭,瞪大的雙眼寫滿驚恐。
“二十年前你毀瞭我的傢庭,帶走瞭我的兒子。”女殺手很滿意自己的活計,瞥瞭一眼俘虜,“還想不起來?被你毀掉的傢庭數目大概都數不清瞭吧?愛管閑事的婊子。我花瞭八年時間,纔找到我兒子的下落,你把他塞在屎一樣的寄養傢庭裏。你把他從母親身邊帶走,他腦子都被你毀瞭,從那以後他一直沒恢復正常。現在他死瞭,你要為此付齣代價。”
她任由俘虜做齣掙紮之舉,走進車道口附近植物長勢過於茂盛的灌木叢中。返迴汽車時,她拿迴瞭昨晚藏匿在林中的汽油桶,裏麵有液體晃動。她不緊不慢地鏇開桶蓋,接著打開駕駛席的車門,等待俘虜意識到自己命運的那一美妙時刻。
社工的尖叫聲被濛住瞭,但她歇斯底裏的模樣讓人心滿意足。殺手慢條斯理地將前排車座澆濕,微笑著傾斜油桶,好讓裏麵的液體灑在女社工的頭發上。油順著她的臉流下,淋濕她傻氣的印花襯衫和肥大的牛仔七分褲。從她布滿蜘蛛狀血管紋路的大腿衝下,在她蹬著白得炫目的網球鞋的雙腳周圍汪成一片。
殺手抖落最後的幾滴液體,將倒空的油桶扔到俘虜身旁的車座,上前一步擰動車子的點火裝置。那俘虜被膠帶濛住的嘴裏發齣號叫,粗糲的喉音讓人感覺刺痛。
“現在你肯正視我瞭,對吧?那你當時把桑尼帶走時,怎麼就不肯聽我說一個字呢。我估計你根本就不記得瞭,是你建議剝奪我的母親監護權的,說我不配再見到我兒子什麼的。”她微笑著直起身,從口袋裏掏齣一盒火柴,“是時候讓你自食其果瞭。”
她沿著火柴盒的擦皮擦動火柴,等火苗燃起便伸齣去遞給俘虜看。她拇指一彈,火柴在空中劃過,落在女人的膝蓋上。
眼見著火焰一躍而起,殺手一臉的滿足。
上帝啊,說時遲那時快,先被點燃的是襯衫,火焰像是一根根貪婪不已的小小手指,伸嚮四麵八方。有那麼一瞬間,她感到有些遺憾,不該捂住那老女人的嘴。尖叫聲總能讓她感到莫大的滿足。有時候她在夢中也能聽見,她體內也會附和著搏動,提醒她想起那些難以忘懷的記憶,想起多年前當她絕望無助之時所發齣的尖叫。那時的她看不到絲毫希望的曙光。
但那樣的境地並未持續太久,而且再也不會重現。
車內火勢所掀起的熱浪很快就逼得她後退瞭幾英尺。這會兒那社工的頭發燒起來瞭,殺手見狀咯咯笑齣瞭聲。就像是小醜波佐①,隻不過火焰代替瞭小醜的一圈紅發。她手舞足蹈地轉過身,彎腰拿起車牌照和螺絲刀。每次離開那座廢棄的建築工地,沿著公路步行前進時,她總習慣性地拿走那兩樣東西。她的車停在兩英裏開外。等有人發現煙氣的來源時,她早就溜之大吉瞭。
她和搭檔都做好瞭每一種意外情況的應對之策。這麼說是誇張,或許吧,但在信任缺失的情況下就會這樣。而且她正在完全遵照他們的計劃行事,隻加瞭些自己的變數。她有多個任務同時執行的能力,況且還有些問題需要解決。
雖然上午纔剛過半,但陽光卻已叫她感到燒灼。這是愛荷華州的七月。她究竟為什麼沒有早早離開這鬼地方呢?一旦時機成熟,這該死的地方她是不會有留戀的。
但時機還未完全成熟。
她兒子死瞭。記憶鉗緊她的胸膛。她可憐的桑尼,他小的時候還算得上可愛,並不完全是長大後的瘋樣。他的發瘋有人要負直接責任。其中的一個現在已經死瞭,那些曾傷害過他的男人們將一個不落地付齣代價。死亡雖叫她興奮,但終究隻是個額外奬勵。迴想起來,隨同死亡而來的復仇纔是最能讓她滿足的東西。
行走之間,她的背上因為暑熱而冒齣細細一層汗珠,叫人感覺不快。汗滴匯聚成細流淌落下來,她走上那條被草叢沒過的車道,一路穿過一片樹叢,圍在中間的是一座外殼已經發黑的農捨。她繞道朝正在下陷、裂口的前門颱階走去,將社工汽車上取下的車牌照丟進一條裂縫,接著繞到屋後。繞過那正在腐壞的房屋後,她徑直走嚮停在百碼開外一座舊棚屋後的汽車。想到車上有空調正在等著她,她心裏感到愜意。而鎖閉的後備箱裏發齣的聲音就不然瞭。
“裏麵夠熱的吧,庫爾特?”她用對話的語氣說道,音量放大,壓過錘擊聲和嘴巴被捂住後所發齣的咒罵聲,“我想你已經瞭解瞭吧,對於你將要迎來的悲慘命運,完全是你應得的啊,誰讓你那樣虐待我可憐的桑尼。”
殺手滑進車座,點燃引擎,通風口爆齣一團溫熱氣體。她小心翼翼地沿著坑坑窪窪的車道倒好車,然後拐上帶狀的碎石路,思緒卻早已飄到瞭腦海中的名單上。那上麵的人,並非每一個都像那蠢社工和庫爾特這般好對付。導緻兒子死亡的那些最富挑戰性的人。那該死的警察,是他追隨著桑尼找到她的藏身處,害得她不得不丟下奄奄一息的兒子逃命。還有與警察聯手的那位精神病醫生。那婊子可能會把兒子錯亂的思維當作瘋子的點對點遊戲。更壞的是,是她乾擾瞭萬斯的行動,破壞瞭他們的戰略。
殺手微笑著,用戴著手套的手從手提袋裏掏齣一副墨鏡打開,架在鼻子上。
那兩人需要特殊對待。而她為他們準備的結局實在是精彩絕倫。
邁剋爾• 弗雷澤暴躁地揮手趕走一隻蒼蠅,然後瞅一眼智能手機。一邊慢慢品嘗早間咖啡,一邊仔細閱讀剋雷格列錶分類網站上的信息,是他每天的例行工作。絕大多數人都沒發現,你能在上麵找到免費物品的可能性有多麼大,人們把信息發上去就是想要彆人來把東西拉走。他的長沙發就是這麼來的,另外還得瞭一組有模有樣的多功能電視櫃。
他同時還鎖定瞭幾個值得日後再訪的地方,而事實證明,再訪所取得的收益更大。在邁剋爾看來,會蠢到邀請陌生人踏足私人地界的人都是蠢蛋,這樣的人不管遭遇什麼都是活該。
他將手肘撐在餐廳裂瞭縫的吧颱上,瀏覽一遍當天的信息,載入鏈接,點開圖片。最終認定今天的分類信息無甚可圖後,他將注意力轉嚮瞭私人廣告,此類信息就算收益較少,但也可供娛樂。
一條熟悉的標題蹦瞭齣來——“黑暗幻想”。這條廣告是兩周前齣現的。他想著還有多少人會和他一樣對此興味盎然呢。
得梅因地區的女性希求狂野的糙漢來幫助我們實現強暴幻想。篩選流程完全匿名。有嚴格措施確保安全、閤法,讓您享受驚險刺激的樂趣。
後麵附上的不是本地電話號碼。
弗雷澤端起廉價的咖啡杯抿瞭一口,視綫依舊定在那則廣告上。他不敢完全確定“刺激”一詞的含義,但是聽起來有下流的味道。這整件事都過於美妙,讓人覺得不可能是真的。說不定是警察下的某種誘餌?但如果雙方都是成年人,那警察也不會浪費時間乾涉。這就意味著這則廣告是閤法的,他剩下的質疑隻是,什麼樣的女人會嚮陌生人發布這樣的信息。
他心心念念地喝完咖啡,將杯子放迴吧颱,惡狠狠地瞄瞭一眼縮在擦痕纍纍的塑料硬吧颱盡頭的店主。他和那乾枯的老婊子一直相處不睦,但幾周前他們達成瞭協議。他會習慣性地走進來,花上一美元五十分無限續杯速溶咖啡,但隻要他在午餐食客進店前離開,她就不會叨擾。作為迴報,他也不會再去割她每天都要開的那輛狗屎汽車的車胎。那老傢夥悄無聲息地端瞭一壺新衝的咖啡過來,放在他麵前,然後側身走開瞭。
他在常去的酒吧裏碰到的那些女人不至於在報紙上登這種廣告。那些女人熟識的大部分男人,都樂得用她們想要的任何方式狠狠愛她們,還會用她們不想要的一些花招。這就意味著,刊登那條廣告的是另一類女人。她們不是妓女、脫衣舞娘或吸毒鬼,她們不認識那樣的男人,對約會這檔子事理都不理,會用下流的方式狠狠愛她們,然後一走瞭之的那種。匿名,是因為刊登那條廣告的女人們玩不起,不能讓人們知道她們乾的好事。
他邊喝咖啡邊沉思。要麼是閑極無聊的傢庭主婦。要麼是某些重權在握的董事會成員,她們一路爬到高層,現在無法擔負代價,讓他人知曉她們實際有多麼變態。
他吹開咖啡上的浮沫,小心地喝瞭一口。弗雷澤的假釋期還剩六個月,不能搞砸再被關進埃納摩薩的監獄。看在上帝的份兒上,他不過是打瞭人事廣告欄上的一個電話罷瞭,他那個懦夫假釋官沒理由發現的,而且如果那邊真有個女人,極度渴望玩真的,狠狠……他臉上浮齣的笑容讓吧颱後的女人不由得退瞭一步。
好啊,那樣一來,他們可就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