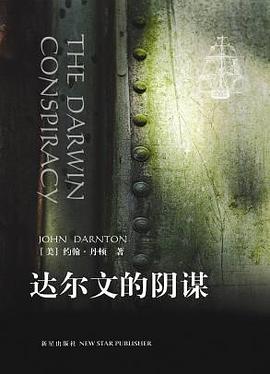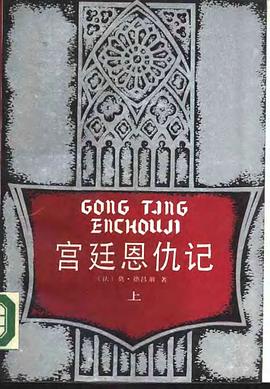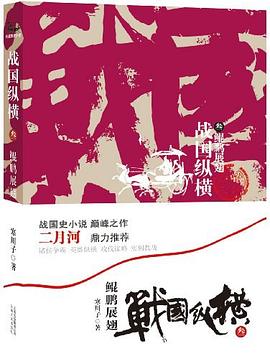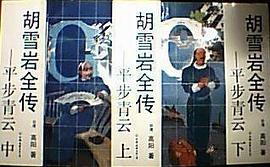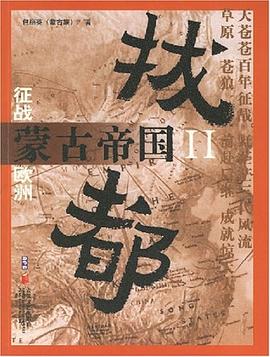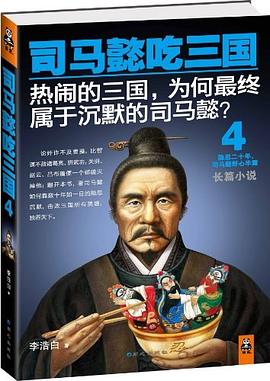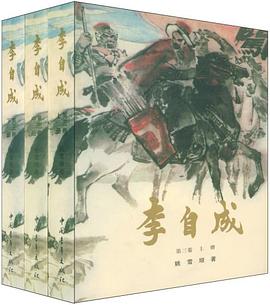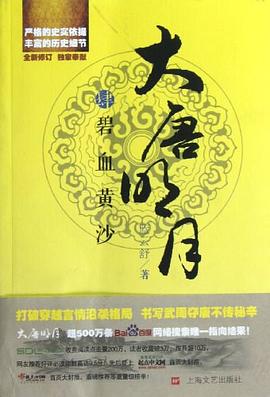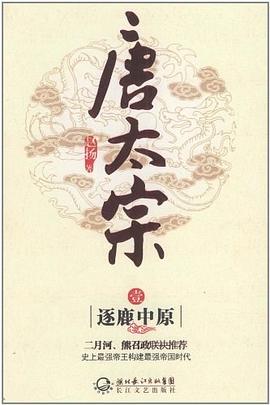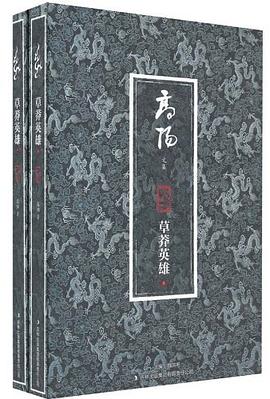序
作者識
瑪麗‧瑞瑙特
亞歷山大的同時代人對他的記載已經全部失傳。我們依賴的是三四百年之後取材於這些現已亡佚的資料而修撰的史書,它們有時說明了資料來源,有時並未說明。阿里安(Arrian)的主要史料來自本故事中的托勒密,但是阿里安的書開篇於亞歷山大即位時。庫爾提烏斯(Curtius)著作的最初幾章已經逸失;狄奧多羅斯(Diodoros)涵蓋的時間段正好,他告訴了我們許多腓力的事,卻對繼位前的亞歷山大著墨甚少。
關於這幾乎占去他生命三分之二光陰的頭二十年,僅存的史料是普魯塔克(Plutarch),以及其他幾書中數處回溯性的敘述。普魯塔克在其亞歷山大傳的這部分沒有徵引托勒密,雖然他應當是該時期的親身見證人之一;因此他大概沒有寫。
我把普魯塔克的敘述放在其歷史背景中作了權衡。我帶著應有的懷疑,採用了狄摩西尼和埃斯基涅斯的演說詞。一些腓力和亞歷山大的小故事取自普魯塔克的︽帝王名將語錄︾(Sayings of Kings and Commanders );若干取自阿特納奧斯(Athenaeus)。
我推測了亞歷山大接待波斯使節的年齡,依據是史書所記載的他們驚異他的提問並不孩子氣。關於列奧尼達斯的性格,以及他搜查王子的箱櫥沒收他母親送來的舒適品一事,普魯塔克引了亞歷山大自己的原話。王子的教師據說人數眾多,列奧尼達斯之外,唯一留下名字的是利西馬科斯(菲尼克斯)。普魯塔克對他似乎不甚重視。亞歷山大有多麼看重他,後見分曉。提爾城久圍不克之時,亞歷山大曾入山遠足,利西馬科斯自吹跟帶大阿基里斯的菲尼克斯一樣強健,年紀也並不更大,堅持要同行。﹁當利西馬科斯變得疲憊不堪的時候,儘管夜已漸深,敵人也近在咫尺,但亞歷山大不肯留下他,而是和幾個同伴一起鼓勵他,幫助他,卻意外發現自己跟大隊走散了,只好在黑暗而極冷的野地上過夜。﹂他獨自襲擊了敵人值夜的一處篝火,搶回一個火把;敵人以為他的軍隊就在左近,撤退了;利西馬科斯守著篝火入眠。留在馬其頓的列奧尼達斯只收到一袋昂貴的熏香,禮物的附牌上反諷地說:他今後不必吝待眾神了。
腓力告訴亞歷山大他應當羞愧自己唱得那麼好—既然有記載,可推斷為當眾演唱──這採自普魯塔克,他寫道,王子再也沒有表演了。其後發生的部落械鬥是虛構的;我們不知道亞歷山大初試戰鋒的時間地點,只能從他攝政的時間回溯。年方十六,他便被全希臘頂尖的將軍委以一項戰略上關鍵的指揮權,完全有信心沙場多年的軍隊會追隨他。到那個時期,他們一定已經很熟悉他了。
與狄摩西尼在培拉的相遇,全是虛構的。然而這辯論家作為末位演講人有數小時可以鎮靜自己,卻結巴了幾句便放棄,雖有腓力的鼓勵也無法繼續,這倒是真事。埃斯基涅斯的說法有八人見證,可以相信;是否該歸咎於他—兩人是宿敵—則不得而知。狄摩西尼向來不喜歡即席演講,但他似乎沒有理由要臨場應變。返回雅典後,他對亞歷山大恨毒已極,是對一個如此年少的男孩子的非同尋常的感情,而且似乎嘲諷過埃斯基涅斯逢迎他。
馴服布克法羅斯的記載見於普魯塔克,細節之豐富,令人不禁揣想它也許源於亞歷山大最愛講的一個餐後故事。我只加了一點:馬匹不久前受過虐待。按照阿里安的記年,它已有十二歲,向國王推銷一匹長年不馴的馬匹是違背常理的。希臘人對戰馬精心訓練,這一匹想必已經訓練過了。然而開價十三塔侖這個天文數字,我無法相信。戰馬是不難替代的(儘管亞歷山大珍愛布克法羅斯直到卅歲)。腓力也許是給他在奧林匹克運動會奪冠的賽馬付了這筆鉅款,而兩個故事被混為一談了。
亞里斯多德在雅典的盛譽始於腓力歿後;他現存的著作時期較晚。我們不知道他實際上教了亞歷山大什麼,但是普魯塔克談到他對自然科學(在亞洲,他一直給亞里斯多德送去標本)與醫學都保有終生興趣。
我假定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觀點當時已經形成。他失傳的作品當中有一卷致赫菲斯提昂的信札,看來,他承認其人的特殊位置。
亞歷山大從叛軍中救出父親一事取自庫爾提烏斯,這史家說,亞歷山大深怨腓力從不承認自己欠了這份情,雖然他不得不佯死求存。
狄奧多羅斯及其他作者都描寫了喀羅尼亞戰役之後腓力的凱旋狂歡,但這些記載無一提到亞歷山大在場。
亞歷山大的性偏好引起過許多議論,貶損他的人傾向於宣稱他是同性戀者,景仰他的人則憤然反駁。
雙方都沒有仔細考慮亞歷山大自己會在多大程度上認為這是不名譽的。在一個以雙性戀為正常的社會,他的三場大婚令他身居主流。他凡事節制,這一點甚受注意;然而在時人看來,他最特立獨行的一點卻是拒絕親狎無力抵抗的犧牲品,如女俘和年輕男奴,儘管那是當時普遍的做法。
他在感情上對赫菲斯提昂的忠誠,是關於他生平最確鑿的事實之一。對此,他表現出公開的自豪感。在特洛伊,當著軍隊的面,他們倆一起在阿基里斯和帕特羅克洛斯的墳前致敬。雖然荷馬沒有說這兩位英雄的關係超出友誼,但是亞歷山大時代的人大多這樣認為。如果他覺得這是不光彩的牽涉,他斷不會自招嫌疑。打贏了伊索斯戰役之後,大流士的被俘女眷以為國王已死,哭喪中,亞歷山大去了她們的帳篷慰問,赫菲斯提昂也隨同。據庫爾提烏斯記載,兩人雙雙步入,衣著相似。赫菲斯提昂個子較高,以波斯標準更英俊。王太后向他行了跪拜禮。她的僕從慌忙提醒她錯了,惶惑之間,她正要向真正的國王俯身,他卻對她說道:「但是您沒有弄錯,老媽媽。他也是亞歷山大。」
顯然他們倆在公眾場合舉止得體(儘管高級將領看見赫菲斯提昂從亞歷山大的肩膀上閱覽奧林匹婭斯的來信而不受斥責,感到厭恨)。肌膚之親未證其實,不願置信的人盡可不信。亞歷山大說過,性交和睡眠使他想起自己是固有一死的凡人,這是有史可稽的。
亞歷山大比他的朋友多活了三個月,其中兩個月,他帶著遺體,從埃克巴塔納行至巴比倫──他計畫中的帝國首都。極盡奢侈的葬儀,華麗龐大的葬臺,向宙斯──阿蒙神諭提出的請求──將亞歷山大已獲得的神格也賜給逝者(阿蒙讓赫菲斯提昂成為英雄),均暗示亞歷山大幾近喪失理智。不久後,他染病發燒,卻在一個聚會上待到夜終。雖然直到他不能行走,甚至於臥床已久時,他仍在推動他的征戰計畫,卻沒有記載說他請過醫生。(他吊死了赫菲斯提昂的失職的醫生。)他疏忽病情的倔強行為似乎是自毀性的,無論是否有意。
他在埃蓋酒神節的經歷是虛構的,但我覺得可以表達一種心理真實。奧林匹婭斯主使的謀殺很多;最終,卡桑德羅斯把她交給受害者親屬來處決。腓力駕崩後,亞歷山大一轉背她就殺了歐律狄刻和她的嬰兒。
她常被懷疑是腓力之死的共謀,但從未確證。狄摩西尼預言性的「神啟幻覺」屬於史實。
普通讀者如想了解亞歷山大即位後的事業,可讀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或阿里安的《亞歷山大遠征記》。兩者在洛布(Loeb)古典叢書中均以希臘文和英文對照。
專有名詞
亞歷山大(Alexander)的真名當然是亞歷山德羅斯(Alexandros);它在希臘北方常見之極,僅在本故事裡,就有另外三個人物和他重名。有鑑於此,也有鑒於兩千年來的習慣,我給了他傳統的拉丁化拼寫。
我同樣為其他幾個為人熟知的名字保留了傳統形式:以腓力(Philip)表示腓力珀斯(Philippos),托勒密(Ptolemy) 表示托勒邁俄斯(Ptolemaios),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表示亞里斯多忒勒斯(Aristoteles);許多地名也如此處理。然而,布克法羅斯(Bucephalus)這個詞散發十九世紀的濫調,揮之不去,我寧可意譯。在亞歷山大的故事裡,沒有一個名稱系統會令所有人滿意;因此,我懷著歉意滿足了自己。
我給腓力的新娘用了歐律狄刻這個名字,儘管那是他賜予她的王室封號,而不是她的本名克莉奧帕特拉,以免和亞歷山大的妹妹混淆。
導讀
關於瑪麗.瑞瑙特/ 鄭遠濤
在彌漫著懷疑與幻滅的二十世紀,瑪麗.瑞瑙特數十年如一日地以小說展現希臘精神(Hellenism),堪稱獨步。然而她的好古並不等於復古,其筆下的古希臘社會的情感與道德,對現代主流價值觀也構成了或明或暗的挑戰。
瑪麗.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本名瑪麗.查倫斯(Mary Challans),瑞瑙特是成年後的筆名。她生於倫敦醫生之家,父母個性扞格帶來的家庭張力,日後在她的作品留下烙印。孩提時,她嗜好牛仔故事,也給她書寫古希臘英雄的冒險埋了伏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延誤了她的中學教育,十五歲才入讀一所著名女校。在學校圖書館,她被柏拉圖《對話錄》的英譯本迷住,畢業前全部看完。因成績優異,她抱着將來教書的想法,被當時專收女生的牛津大學聖休斯學院(St Hugh's College)錄取,主修英語。
「牛津造就了我,」後來瑞瑙特喜歡說。然而在彼時那保守年代,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學也不免給她帶來揮之不去的邊緣感。無論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響她一生的兩位老師:希臘學教授吉爾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後來以《魔戒》成為一代文豪的語言學教授托爾金(J. R. R. Tolkien)。
默雷的講課令她重燃對柏拉圖的熱情;在柏拉圖的熏陶下,她建立起對個人的信仰,對「賢能政制」(meritocracy)的嚮往,當然更少不了對靈魂之愛的追求。它們均貫穿在她重構的古希臘世界中。
大學時瑪麗決定畢業後從事寫作,並不顧父母反對,獨立過了幾年一邊打工、一邊筆耕的生活,終因營養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養。一九三三年夏,將滿廿八歲的瑪麗徒步旅行重訪牛津,在離母校不遠的拉德克利夫醫院(Radcliffe Infirmary)門外歇息時,做了一個影響命運的決定。她省悟到沒有人生體驗的作家不會是好作家,而在那古老的醫院中,生老病死永恆地上演着。她當即謁見院長,說服讓她留下學習護理,從此步入艱苦的學員生涯。
她在拉德克利夫邂逅見習護士朱莉.穆拉德(Julie Mullard),兩人情投意合,後成為五十年的終身伴侶。感情的安定給瑞瑙特的小說帶來莫大影響;在她八部歷史小說中,最著力刻畫的愛情即是相濡以沫的伴侶關係。
完成學業後,瑪麗從事護理,利用工餘和假期寫小說,處女作《愛的意義》(Purposes of Love )出版於一九三九年戰雲密佈的倫敦。二戰爆發,瑪麗和朱莉響應政府動員令,先後在多地醫院照料傷兵,並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醫院服務。醫院中擔任勤雜工的「良心反戰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予瑪麗以不可磨滅的印象,後來終於被她寫入《御者》(The Charioteer )中。
戰後她離開護理行業,專心創作。直到離開英國遠赴南非定居前,瑞瑙特共出版五部小說,皆以當代為題材,背景多少涉及她所熟悉的醫院與醫務人員,致力於刻畫他們的內心世界,尤其是感情生活。同性情慾(homoeroticism)或女同性情慾(lesbianism)在這些書中或隱隱若現,或呼之欲出。半自傳性的《相好的姑娘》(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 1944 )題目就蘊含女同性愛的意味。《瑪麗.瑞瑙特的多副面具》(The Masks of Mary Renault )一書作者齊布爾格(Caroline Zilboorg)認為它「迎頭面對了雙性戀女子要在異性戀世界中劃定一種女同性戀關係的困境。」並指出「瑞瑙特最初五部小說的笨拙結尾證明了她故事的駭俗本質。」
一九四八年定居南非是瑪麗.瑞瑙特寫作生涯的轉捩點。在這個新國度,她和伴侶朱莉結識了不少年輕的演員和舞蹈家,多數是男同志,他們的聚散離合激發了瑪麗的靈感,寫出《御者》(1953)。小說設定為二戰烽煙下的三角戀愛故事,主人公羅瑞是傷兵,他要在純真懵懂的「良心反戰者」安竹和他從前的學長、如今世故甚深的拉爾夫之間抉擇—不願面對性傾向的安竹,不可能與之經營幸福;而拉爾夫流連於地下同志圈的習性,也似乎無法給羅瑞帶來安穩的愛情。作者暗示,在一九四〇年代的英國,一個同性戀屬於非法的社會,尋求性與愛的羅瑞除了妥協別無他途。「御者」是柏拉圖《斐德羅篇》(Phaedrus )的一個意象,象徵靈魂的駕馭力。此書大膽寫實,以至瑞瑙特的美國出版商退還手稿,六年後才得以在美國推出。時至今日,此書已被公認為現代同志文學的里程碑之一,與維達爾的《城市與鹽柱》(The Cityand the Pillar )和伊薛伍德的《柏林故事集》(Berlin Stories )相提並論。
大段徵引柏拉圖、古典意象豐富的《御者》是瑞瑙特創作的分水嶺;此後她沿著歷史長河繼續上溯,直接踏上那早已消逝的古希臘世界,最終寫出八部考據嚴謹、栩栩如生的歷史小說,步入大師之列。轉型滿足了她長久以來的抱負和興趣,更解放了她的想像力。齊布爾格說,藉着古代背景,瑞瑙特得以自由書寫她最感興趣的主題──「戰爭、和平、英雄主義、職業生涯、女性的角色、性表達,還有男男女女的同性愛和雙性愛。」
一九五六年的《殘酒》(The Last of the Wine ) 以伯羅奔尼撒戰爭(431–404BC)為背景,講述在柏拉圖老師蘇格拉底門下的一對雅典情侶十三年的流離。呂西斯與阿列克西亞的關係,再現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戀習俗:較年長的「愛者」(erastes)要擔當他傾慕的少年「所愛」(eromenos)的精神導師。兩人彷彿是另一時空的拉爾夫與羅瑞,因生活在一個推崇男風的英雄主義時代,而能更加高貴而長久地相愛。戰爭與和平交替,暴民與寡頭輪番上台,雅典由盛而衰的歷程如長卷一樣徐徐鋪展。這小說一舉奠定了瑞瑙特作為歷史文學大師的地位,也確立了她用得爐火純青的敘事手法—第一人稱回憶體的成長小說。
瑞瑙特在希臘之旅中參觀了阿瑟.伊文思修復的希臘史前文明遺蹟—克諾索斯王宮,相傳是雅典王子特修斯(Theseus)勇闖迷宮,殺死牛頭怪的地點。回到南非後,她根據歷史學者的理論與考古學的新近發現,剝離傳統神話中可信的元素與混雜的附會,將特修斯一生的傳奇演繹為兩部小說—《國王必須死去》(The King Must Die, 1958 )和《海裡來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1962 )。喜愛遠古文明和人類學的張愛玲十分賞識《國王必須死去》,曾對採訪她的作家水晶說她「看得津津有味」。
在南非,瑪麗和伴侶朱莉在一座臨海獨棟木屋住了多年。帶鹽味的輕風,滑翔的海鷗和遠遠的航船,勇敢的泳者和衝浪少年,與她筆下的另一個海洋文化—古希臘世界一樣充滿生機。但「外面的世界」並不如此自由。一九六〇年代伊始,隨著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深化,反隔離的瑞瑙特愈來愈捲入政治生活中。
她上街示威,參加抗議團體,到社區為政黨拉票。然而政治講求集體行動,處處需要妥協,與這位藝術家對「個人」的信念格格不入。因此,她雖然在一九六四年同意出任國際筆會(P.E.N.)開普敦分會的會長,並與圖書審查作長期鬥爭,但年事的增長、對政治的失望,令她淡出了運動,重投想像世界。她相信作家的道德責任首先在於喚起個人的良知與覺醒,筆才是她自己最好的武器。一九六六年,她出版了新作《阿波羅面具》(The Mask of Apollo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危機四伏的希臘,一個周遊列邦的演員見證了柏拉圖為了實踐政治理想,兩度遠赴西西里,輔弼僭主狄奧尼索斯二世做「哲人王」,最終慘淡收場的史事。
作者在按語中寫道:「這時代濃厚的政治幻滅感,在智識上表現為對於理想制度的探尋,在歷史上表現為亞歷山大的橫空出世。」她下一本書便寫了這位應時代而生的早慧天才,並一發不可收,最終為他寫了四部著作,包括著名的「亞歷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Fire from Heaven, 1969 )、《波斯少年》(The Persian Boy, 1972 )、《葬禮競技會》(Funeral Games, 1981 ),以及一部傳記《亞歷山大的本性》(The Nature of Alexander, 1975 )。
賢能政制是瑞瑙特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早在一九五○年代,她已在特修斯故事中虛構過具有賢能政治色彩的團體—「鶴群」(Cranes);而在《波斯少年》中,征服者亞歷山大傾力要建成一個民族平等、選賢任能的帝國。正如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名著《西方哲學史》中闡明,馬其頓崛起前,各自為政的城邦之間長久內耗,已經令希臘文明飽受外患,難以為繼,而亞歷山大的政策「給有思想的人們的頭腦帶來四海一家的觀念;以往對城邦的忠誠與(在較小程度上)對希臘民族的忠誠看來已不合時宜了。在哲學上,這種世界主義觀點始自斯多葛派,但在實踐上它開始得較早—始自亞歷山大。」
儘管亞歷山大的夢想終因英年早逝而化為碎片,成了權慾的血腥爭奪品(《葬禮競技會》的題材),他的事業畢竟有功於希臘文明的傳播與保存;這為世界主義的羅馬帝國奠下了文化根基。
「他的臉多年來縈繞在我的心頭;」瑞瑙特給一位牛津舊友的信上談起亞歷山大,「迷人的眼睛,頭髮從額上躍躍欲起,還有那二十來歲想必已飽經風霜的美—太陽曬得他皮膚近黑,頭髮近白。」這形象符合《波斯少年》中滄桑的亞歷山大,他在《天堂之火》裡並非如此,此書只從他五歲寫到二十歲即位為止。
相傳,奧林匹婭斯懷著亞歷山大時夢見漫天遍地的一場大火,燒遍了世界。題目中的「火」便是亞歷山大,「天堂」指他「神裔」的身世;瑞瑙特採用史詩文學中的重複修辭法,在本書裡常以shining(光采照人、光華熠熠)一詞形容他,喜愛溢於言表。
作為歷史小說,《天堂之火》同時是一部偉大的成長故事。作者以象徵手法鋪陳亞歷山大童年的張力──失和的父母對他的爭奪:故事開始時纏繞他腰間的蛇,是母親捆縛他的、他後來努力掙脫的紐帶,而小說結束時勝負未定的鷹蛇搏擊(鷹是宙斯—父性—的象徵物),則暗示父母雙方的影響在他餘生中將繼續起伏消長。主人翁生為國王之子,父親是全希臘的霸主,武功赫赫,母親則要他相信自己是神裔。
他一方面受斯巴達式的紀律訓練,一方面充滿尚古情懷,以神話英雄阿基里斯為楷模,是荷馬史詩在精神上的最後一個傳人,立志要用無所畏懼的戰鬥來證明自己猶勝乃父。他師從大哲亞里斯多德學習治國、倫理和科學,卻比亞里士多德更富於想像力與熱情,又能在實踐中超越老師的種族偏見。他情感細膩,卻由於父親濫交的反激作用,秉持著近乎禁慾的節制。家庭張力使他從小向外尋求友誼:從衛隊的營房、馬廄的僕役、波斯流亡者那裡增長見識,得到安慰;受《伊利亞特》英雄情誼的熏陶,他與赫菲斯提昂更成了生死相隨的伴侶;他對年少的波斯使節心儀、跟「蠻族」王子蘭巴若斯結下友情,也預示著《波斯少年》中他對巴勾鄂斯的跨種族愛戀。
齊布爾格指出,不在父與母、男性與女性之間作終極的選擇,而是糅合兩種力量來塑造自我,正體現了亞歷山大的卓越。
二〇一〇年,出版已屆四十載的《天堂之火》入圍專家評選的「曼布克遺珠獎」(Lost Man Booker Prize)決選名單,這小說的持久魅力可見一斑。二〇一四年夏天,英國Virago 出版社發行了新版「亞歷山大三部曲」,邀來早年受惠於瑞瑙特小說的歷史學家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撰寫前言,其中一段值得抄錄於下:
瑪麗.瑞瑙特弔詭的地方,以及她令古代世界起死回生的非凡成就之關鍵,在於她打破成規同時又回首陳跡,既激進又保守。借著亞歷山大三部曲,同性愛小說第一次躋身主流文化;但內中對民主制的鄙視、對英雄主義的理想化呈現、對女性的不信任,又深深忠實於早已消逝的亞歷山大時代。正如最佳歷史小說毫無例外地做到的那樣,它迫使讀者拋開自己的條框,接納一個已消逝世界的原貌。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