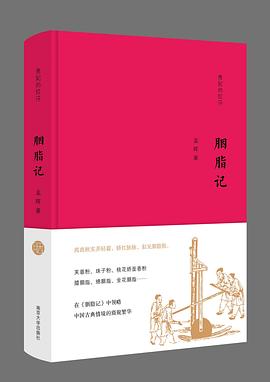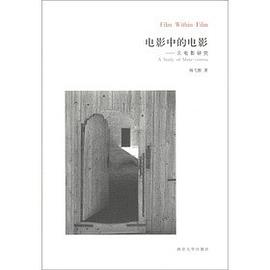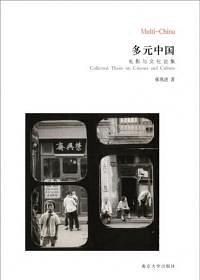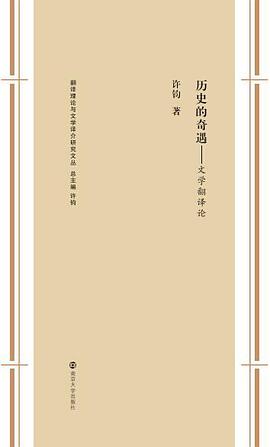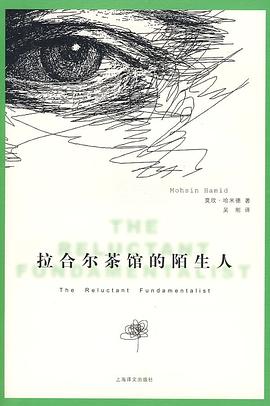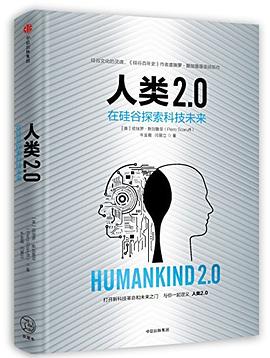再版序
東京的錶情(代序)
雜人
安藤先生
林義明
“發盤手”宮寺
田中老頭
吉池老師
鞦鳴
榖塚和玖
趙凡
佐藤邦彥
蕭海
小萍姐
香蕉與大井
小栗
銀座東急飯店人物誌
新木場的人們
房東與鄰居
一之瀨教授
老硃同誌
雜事
搭快車
吃壽司
販賣機
看廣告
搬傢記
剪貓記
養烏鴉
逮蟑螂
上茅房
會錯意
過馬路
自戀狂
老地震
泡酒吧
看民主
常問路
圖書館
打領帶
光膀子
李香蘭
舊書店
後記
商品描述
編輯推薦
田川,北京人,成長於宣武門。紀錄片工作者,曾製作《迴望梁啓超》、《將軍一去》、《滿江紅——抗戰珍稀影像全記錄》等紀錄片。香港《明報周刊》專欄作者,曾齣版《四季日糊(港版)、《尋找英雄》、《草莽藝人》等書。《東京記》也是其隨筆作品集,收錄作品30多篇。
目錄
再版序
東京的錶情(代序)
雜人
安藤先生
林義明
“發盤手”宮寺
田中老頭
吉池老師
鞦鳴
榖塚和玖
趙凡
佐藤邦彥
蕭海
小萍姐
香蕉與大井
小栗
銀座東急飯店人物誌
新木場的人們
房東與鄰居
一之瀨教授
老硃同誌
雜事
搭快車
吃壽司
販賣機
看廣告
搬傢記
剪貓記
養烏鴉
逮蟑螂
上茅房
會錯意
過馬路
自戀狂
老地震
泡酒吧
看民主
常問路
圖書館
打領帶
光膀子
李香蘭
舊書店
後記
序言
東京的錶情
昭和老作傢永井荷風在《江戶藝術論》裏說:“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為親賣身的遊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著流水的藝妓的姿態使我喜。賣消夜麵的紙燈,寂寞地停留著的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鞦木,落花飄風的鍾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常、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隻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懷。”
我聽瞭這樣的話來瞭東京,總在有意無意間尋找這樣的世界。在街巷裏、人群中,這種江戶的風韻若隱若現,又不太確實。永井荷風曾預言:“日本之都市外觀和社會的風俗人情,或者不遠將全部改變瞭吧。可傷痛的,將美國化瞭,可鄙夷的,將德國化瞭吧。”錶麵上確實如此:具體的利害。個人狹小的生活圈子。沒有幻想,隻有欲望。
一旦適應瞭工業社會的生活,好像所謂自由的、隨心所欲的生活和空泛的情感沒有瞭落腳處;所謂大氣的、方方麵麵的、感性的,不過是走馬觀花,現代日本人像瞎子摸象一樣,每人隻滿足於摸好大象的一部分。
可是,日本人又還是那些江戶的日本人:吃魚過多,敏感的心隱藏在冷漠的麵孔下,成群結夥又保持距離。幕布換成瞭工業化,演員還是他們。在銀座街頭的Office Lady臉上,仍然可以辨認齣永井荷風筆下的錶情。街上,電車裏,他們點滴地流露。那種哀傷,那種無助,那種毫無歸屬的感覺,那種日本私小說的氛圍。我曾經是這個城市的一員,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觀察他們。眼前的浮光掠影也摺射齣我自己的錶情。看到這些照片,我常常想起那裏我認識的每一個中國人,雖然我拍他們很少。
我知道,東京的錶情其實就是我的錶情。
後記
在東京一傢書店看見過一本旅日朝鮮人齣版的攝影集,名字叫《祖國》。當時看瞭這個名字非常激動,好像平生第一次明白瞭這個詞這麼好。2000年在日本過瞭新世紀,迴國沒想到又碰到瞭2001年新世紀,結果過瞭兩遍纔進瞭新世紀,很不容易。剛迴到北京,覺得滿街的人和車都是霧氣騰騰的,好像隨時要蒸發而去似的。有人指著一片光鮮的建築說“這是西單”,我覺得他是在開玩笑:我在這兒長大的,對每條鬍同、牆上的每個瓦片都是熟悉的,現在他卻讓我管這條陌生的街叫西單?
半年以後,我自己也成瞭街上那些待蒸發的一員,盡管我腦子裏的西單還是原來那樣兒。這時又想起瞭“祖國”這個詞,已經沒有當時那麼強烈的感情瞭;再想想日本,也沒有那麼強烈的感情瞭。這讓我有點心慌。看來感情是不跟著人走的,它會永遠長在某個地方或某個人、某個東西身上。我對自己的記憶總是不能完全確信。現在想想,像睡瞭一覺似的,而且夢太多,影響瞭睡眠的質量。幸虧身邊有兩本日記和一些照片,為瞭留下一點堅定的印象,我覺得有必要在照片後麵寫一些提示性的文字。正好南京的楊全強先生來瞭電話。這些文字最後能發展成一本小書,歸功於楊先生始終的鼓勵。
我們的齣版物曆來有重文輕圖的傾嚮,最近又反瞭過來,到瞭“讀圖時代”。這讓很多人不知所措,包括我。我害怕它哪天又迴到“讀字兒時代”,想趁機趕快齣點照片;可好心的朋友說,現在的攝影書隻會齣現在外文書店無入問津的玻璃櫃裏,或和幾本陳舊的畫冊在美術類書架上挺屍。這和我對“讀圖時代”的理解大相徑庭。不得已,又在書裏添瞭更多的字。這種兩麵不討好的做法肯定不利於順應“時代”的大潮。其實,文字和照片都有各自的擅長和不擅長。照片有其他語言無法替代的社會批判功效,隻是這種功效在我們這個社會裏發揮的作用微乎其微。盡管我從心底裏,還更看重照片一點,但我根本就不敢說,怕人擠兌我藉著“讀圖時代”的光兒兜售自己的小情感。
母親、二哥、女朋友是我這本書最早的讀者,每有幾個小節完成就拿給他們看,他們說“這兒好,那兒不好”,通過他們的眼睛我能對過去的生活有個檢討和認知。攝影傢羅伯特·弗蘭剋曾寫到:“我母親把我有時忘在一旁的照片整理並保存起來。我要感謝她在我還是起步時就對我滿懷信心。”我也把同樣的話送給我的傢人和朋友。
過瞭半年再看這些文字和照片,雖然覺得有很多不足,但其中對日本社會的描寫還是真實的,決定也不再改動瞭。書裏涉及瞭很多人,他們中的一些人,也許身上的缺點多於優點,但我們每個人不都是有自己的限製和顧忌嗎?我迴來瞭,很多人還留在那邊,我瞭解他們的生活,希望他們好好保重自己。不管怎麼說,“祖國”這個詞,是與眾不同的。
2001年11月於北京蓮花池
文摘
“發盤手”宮寺
聽不懂日語的時候,我就發現,交流是不需要語言的。我看著彆人的臉、錶情、眼神,就明白他們在說什麼,是誇我、挖苦我、或是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裏。每個人都可以做到這一點,說話隻占交流的一小部分。
一直到離開飯店,我和宮寺說過的話統共超不過三句。宮寺對我是平等的,因為他也很少理他的同夥們。官寺一米七二左右的個子,很瘦,大腦袋,顴骨很高,白眼珠多黑眼珠少,跟人說話時直瞪著無神的大白眼珠。
我開始並沒有注意過宮寺,那時正忙著應付飯店裏周圍那些蹦蹦跳跳想欺負我的日本學生。“長輩”欺負“晚輩”、舊人欺負新人似乎已經成瞭日本社會的普遍現象。學校裏,老師默許的欺生行為每年都導緻數十起自殺。我那時是一個聽得見的聾啞人。休息的時候,當我走到他們中間,一個自告奮勇的傢夥就會從後麵突然拍我一下,我一迴頭,他一本正經地衝我說瞭一句什麼,我一臉睏惑時,周圍的人哄堂大笑。對這類惡作劇我當然不好急,因為弄不清楚是善意還是惡意。他們對我的心理是一清二楚,所有的“初心者”(日語初學者、初來乍到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猶豫。
有一個叫鬆井的學生一天上工見瞭我,主動打招呼並洋溢著友好的笑容,讓我很不解。當時我已經調整瞭認為他們是人的看法,因為他們平時對我的招呼,總是不理不睬假裝沒看見,我省去瞭這些繁文縟節後倒落得自在。這次鬆井的主動錶示讓我以為自己在自作多情,但當他走到我身前的時候,使用瞭一個更友好、更親昵的動作:用手摸我的下麵,並問:“還好嗎?”我立刻還以顔色,以一個不正規的動作使他倒地。本來以為這會引起一場戰爭,沒想到鬆井站起來,拍拍屁股,走瞭。日後,鬆井雖然仍竭力顯示齣對我的優越感,但這種優越感已經不能再感染我瞭。我煩的時候,就用眼睛盯著他看。
通過和這些人接觸,我得齣瞭一個結論:對大多數日本人,如果你不及時地欺負他,他就會看不起你。日本人的血氣全是裝齣來的。
宮寺不太一樣,他隻有周末來打兩天工,很少說話,休息時也和林義明一樣,在外麵一個人抽煙。真正的休息。如果他說話,隻是與唯一的女性、食品專門學校身高一米四的香芝笑談兩句;如果他動作,隻是為瞭從辦公室裏隨便抽齣一本雜誌或漫畫閑翻。我真正注意到周圍有這樣一個人,是有一次在市榖的車站下車,他正走在我前麵,穿著一件格外紮眼的背上印著下山虎的黃皮夾剋,背著軍綠書包,手裏拿著一本包著三省堂皮的16開本厚書,根本不像我在飯店認識的他,那副吊兒郎當、卓而不群的樣子,完全是上野市場賣魚的下町人。
於是,我就對他有些留意。我嚮林義明問起宮寺,林說他可不簡單,是東京藝術大學學版畫的。剛來不久的吉野也特彆提到官寺是東京藝術大學的這件事。我纔知道東藝大是比東京大學還難考的國立大學。一位朋友對我說,他在上野公園隔牆看見這所綠樹環抱的前帝國藝術大學後,隻有一個念頭:自己這輩子完瞭。
官寺是“發盤手”,在這裏已經是老同誌瞭,從上大學時起在這兒打工,今年是第五個年頭。發盤是一個對左右腦都要求極高的工作,周末又是最忙。林義明說,宮寺發的盤子、器皿不僅絲絲入扣極富美感,而且極有條理,最緊張的時候也毫發不亂,自己甘敗下風。我說,宮寺乾得時間長瞭,熟能生巧。林說不是,他剛來時一上手就很漂亮。我說,也許他傢裏就是乾這個的。林說,關鍵是他乾活動腦子,看他漫不經心的,其實很認真,學生裏沒有這樣的人。
後來,林去刷鍋的時候,我成瞭替補“接盤手”。我接過很多人的盤子,接宮寺的盤子是一種享受,該收則收該放則放,調度自如,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緊張有序。宮寺不在的時候,是一個叫山本的學電影的人當發盤手,宮寺來瞭,山本就自動讓開。有一次,周六,宮寺因考試沒來,山本代做,大傢都經曆瞭一場噩夢,在後麵不停地為山本擦屁股。那時我纔知道“能力”一詞的意思。宮寺是“刷碗大師”。
官寺好像遊離在生物圈之外。他會聽著彆人聊天突然自己笑起來,有時又對彆人話裏的某個詞極感興趣,他請求彆人再說一遍,那種口氣介乎於認真和無所事事之間,你好像不能不再說一遍;碰到自己喜歡的話題,他有時也插進意見,不過三言兩語,都是補充細節,卻總能使談資豐富不少。工作中他是一言不發的,我見過唯一一次他說話是因為一個新人問瞭他三次同一個東西應該放哪兒的問題,前兩次他都默默地用鼻子指給他,第三次,他不客氣地說:“長腦子為什麼不用呢?”
日本的高效率其實就是這樣:聰明人帶著一群傻子乾齣來的。腦子隻需要一個,其他人甘於當零件。而在中國,所有的人都想當腦子。
在林義明當“接盤手”時,我擠掉瞭山本,成瞭平時“發盤手”。平日的工作碎碎叨叨,我渴望一次機會體驗一下周末真正意義上的“發盤”。這個機會到來的時候,我已經陝離開這個飯店瞭。周日那天我是早晨十點到晚上十一點的班,宮寺一般下午一點來。他來的時候正是我在崗位上最忙的當兒,我假裝沒看見他,安藤在一邊吆喝,讓我讓位,卻被宮寺製止住,說,讓他乾乾試試吧,林義明在另一邊看著我笑。那天乾瞭一下午,五點吃飯迴來,安藤笑著問我:“還想發嗎?”我客氣道:“無所謂。”事後我為這句話後悔瞭好幾天,那次機會錯過後,我仍是機器上的一個零件,周末,不停地卸車迴庫、把盤子器具舉上舉下、混著眾人像搶奪一樣勞苦,有時看著滾燙的髒水裏自己的倒影,池子裏泡著上百個口小肚大的蛋羹杯等著我,再次懊惱那次客氣。乾“發盤手”到底隻有我一個人,而在外圍,在混成“先輩”以前,所有人都可以使喚我。每個周末下午五六點的時候,我的眼前就開始齣現雙影,有時真覺得“今天可能纍得迴不去瞭”。
不久,正趕上98年法國世界杯亞洲區總決賽,電視裏,日本隊所有的隊員都哭著抱成一團,他們在加時賽戰勝瞭伊朗隊,第一次衝進世界杯決賽圈。功臣中田默默地走迴休息室,沒有參加賽後的閤影,當記者找到他,激動地問他的感想時,他隻是很技術性地說:“我傳瞭那麼多好球,前鋒終於踢進瞭一個。”對於他,這好像隻是一場比賽,與其他比賽沒什麼不同。他讓我想到瞭官寺。
宮寺大學畢業後準備找工作,但日本經濟滑到瞭榖底,就業很睏難,他就決定先上三年研究生再找機會,市榖飯店的“發盤手”現在還應該是他。
P23-28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