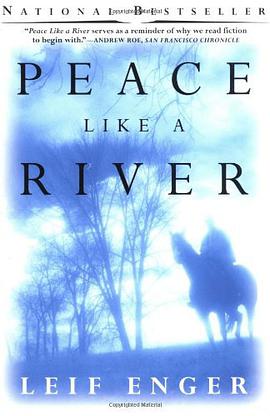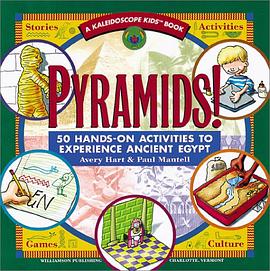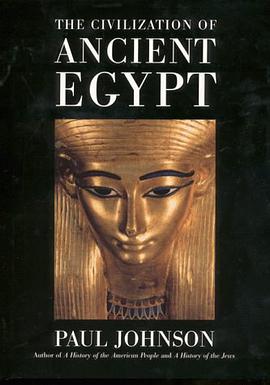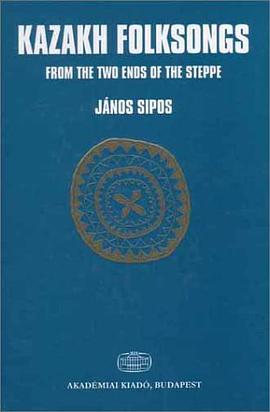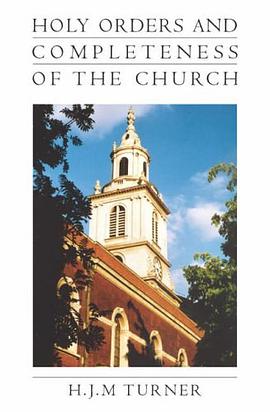
Holy Order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Church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出版者:Melrose Books
作者:H.J.M. Turner
出品人:
页数:0
译者:
出版时间:2005
价格:0
装帧:Hardcover
isbn号码:9781905226009
丛书系列:
图书标签:
- Holy Orders
- Sacraments
- Church Theology
- Ordination
- Priesthood
- Ministry
- Ecclesiology
- Catholic Theology
- Anglican Theology
- Sacramental Theology
下载链接在页面底部
具体描述
权力的界限与信仰的回归:一部关于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政治的深度剖析 《圣职与教会的完满性》(Holy Order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Church)并非一本专注于教义革新或仪式细节的著作,它将历史的聚光灯投向了中世纪西欧权力结构最核心的矛盾点:神权与王权的永恒角力,以及这种角力如何塑造了“教会的完满性”这一复杂的概念。本书旨在揭示,教会如何在中世纪的政治风暴中寻求其神圣权威的完整性,以及这种寻求在现实政治的泥沼中如何扭曲和异化。 本书的结构清晰,分为六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力求提供一个多维度的历史分析框架,而非简单的编年史叙述。 第一部分:神权基础的构建——从格里高利改革到教皇至上主义的萌芽 本部分深入探讨了公元十一世纪初,以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为代表的“格里高利改革”如何为教会在世俗事务中争取独立地位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重点分析了“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的深层意义。这不是简单的任命主教职位的权力之争,而是关于谁拥有对上帝所赋予的属灵领域(Spiritual Realm)的最终解释权和管理权。 作者细致考察了教皇法典的编纂工作,特别是关于“教皇普世性”(Papal Supremacy)的论述如何从有限的管辖权扩展到对所有基督教君主的道德约束力。我们审视了早期教皇如何利用教会法(Canon Law)来构建一个与世俗君主制并行、甚至凌驾于其上的法律和行政体系。教会的“完满性”在此阶段被定义为一种不受世俗侵犯的、神圣授权的独立性。 第二部分:双重剑的理论与实践的错位 中世纪政治思想中著名的“双重剑理论”(Doctrine of the Two Swords)是本书讨论的基石之一。根据这一理论,上帝将属灵之剑(教会)和世俗之剑(君主)授予人类,两者本应协同运作,以维护基督化社会。然而,本书着重剖析了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是如何不断失衡的。 通过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格里高利七世在卡诺莎之辱(Walk to Canossa)事件的详细重构,我们看到理论的僵硬性与政治的灵活性之间的巨大鸿沟。教会成功地迫使皇帝屈服于教皇的道德权威,但这种胜利的代价是:教会必须更多地卷入世俗的政治联盟与军事干预中,从而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世俗权力的弊病。教会的“完满性”开始受到其自身军事和财政需求的侵蚀。 第三部分:教皇国的世俗化——政治机器的运转 本部分是全书最具批判性的分析之一。它考察了教皇从一个纯粹的属灵领袖,如何转变为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城邦君主。教皇国(Papal States)的管理、财政系统的运作、以及教皇对外联姻与军事同盟的策略,都被置于显微镜下进行考察。 作者引入了“教会作为领主”的概念,探讨了教会庄园的征税、军事征募与世俗法律的采纳,这些行为如何与教会宣称的“贫穷与纯洁”的理想产生尖锐的冲突。教会的“完满性”在此阶段面临内部危机:一个既要管理天堂,又要管理尘世土地的机构,其精神权威如何保持其独特的超凡性? 第四部分:异端、修会与教会内部的张力 教会的“完满性”不仅受到外部世俗王权的挑战,也受到内部对纯洁性要求的回应的冲击。本部分聚焦于十二、十三世纪新兴的修会(如方济会和多明我会)以及与此相伴的异端运动(如卡特里派)。 我们分析了这些运动如何将教会的世俗化视为对其神圣使命的背叛。当教皇拥有奢华的宫廷和庞大的军队时,新兴的传道者呼吁回归使徒时代的简朴生活,这直接挑战了罗马教廷的制度合法性。本书详细比较了教会镇压异端(如阿尔比派十字军)的残酷手段,以及教会如何试图通过吸纳、利用或改造修会运动来维护其作为唯一正统的“完满”地位。 第五部分:法兰西的崛起与教权的衰落前夜 十四世纪初,随着法兰西王权(特别是腓力四世)的崛起,教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抵抗。本部分重点研究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与腓力四世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关于教会财产税收权和司法豁免权的斗争。 “阿维尼翁之囚”(Avignon Papacy)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迁移,更是教权在世俗政治力量面前的实质性屈服。本书认为,当教皇的宝座被置于法国君主的阴影之下时,其宣称的普世、独立和至高无上的“完满性”在现实中宣告破产。教会的行政中心虽然仍在,但其精神的独立性和绝对权威性受到了永久性的削弱。 第六部分:完满性的重塑与历史的遗产 最后一部分对全书的论点进行了总结。作者认为,中世纪教会对“完满性”的追求,是一个动态且充满矛盾的过程。教会试图成为一个完美的、无瑕的“上帝之城”,但为了在世俗的“人间之城”中生存和掌权,它不得不采纳世俗的工具、制定世俗的策略,并最终承担了世俗机构的局限性。 本书的结论是,中世纪教会的“完满性”并非一个静止的神学状态,而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它是在不断妥协、斗争和吸收外部压力中形成的一种复合体——一个在精神上至高无上,在世俗运作中却深陷泥潭的庞大机构。本书旨在提供一个严谨的历史视角,审视中世纪的权力格局如何定义并最终限制了教会所能达到的“完满”程度。它迫使读者思考:在一个要求绝对纯洁的机构,其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其神圣权威的纯粹性之间,存在着何种不可调和的张力。
作者简介
目录信息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图书下载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