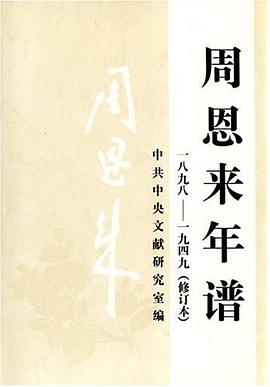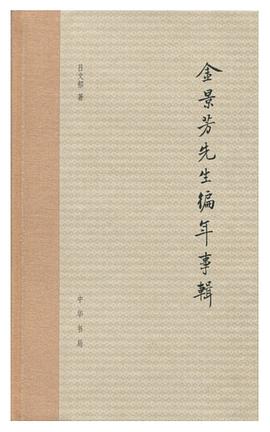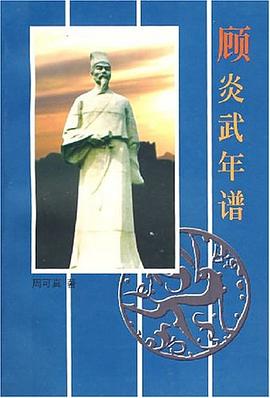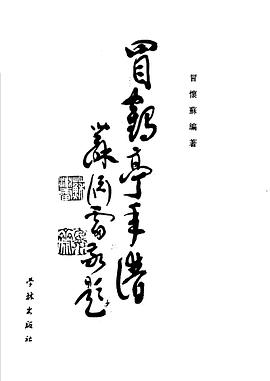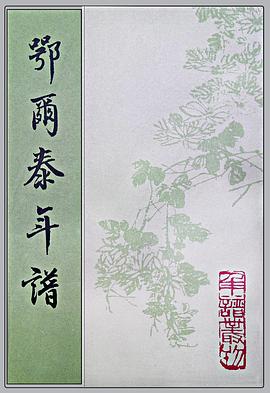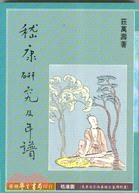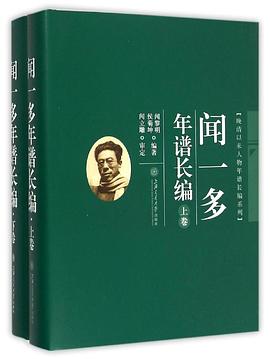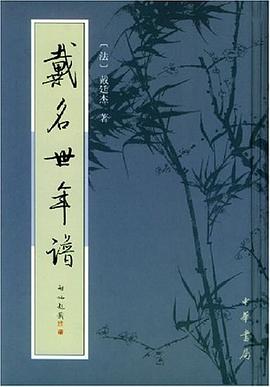
戴名世年譜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2025
清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是震動一時的文字獄大案,案涉安徽桐城戴、方兩大名門望族,《孑遺錄》和《南山集》的著者戴名世“從寬免淩遲,著即處斬”,而另一主犯方孝標也因《南山集》中提到他“語多悖逆”的《滇黔紀聞》遭至戮屍。株連者不計其數,凡兩傢親屬朋友,或被殺戮,或遣戍為奴,其中不少都是知名學者文士,桐城派古文開創者方苞即在其列。
康熙五十年,禦史趙申喬疏參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纔放蕩,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又說“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闆,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清華?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謹之戒”(《清聖祖實錄》捲248)。這種理由,按理罪不至死,更不該株及九族。但康熙一句硃批:“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竟釀成清史一大文字獄,恐怕連趙申喬也不會想到吧。
來新夏教授認為,論者頗多以這段話來作為戴名世緻罪之由。實際上這一檢舉內容純是一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誅心之論,充其量隻不過是過去有些不恰之作,而入仕後沒有毀版的曆史問題而已,何至於羅織罪名而興大獄呢?我一直對此有所置疑。認為幕後必有某種不可告人的隱秘。在讀趙申喬後裔保存的趙申喬原奏疏結尾處有一段話,曾引起我的注意,文稱:“臣與名世,素無嫌怨,但法紀所關,何敢徇隱不言?為此特疏糾參,仰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謹之戒,而人心鹹知悚惕矣,伏侯皇上睿鑒施行!”這段話透露瞭一種信息:身為總憲的趙申喬糾參某些官吏的有罪,是他職責所在,參奏中隻需列舉事實,根本無需在疏文中洗清個人與被參劾者間有無嫌怨的問題。《聖祖實錄》中把這幾句洗刷關係的話刪節掉證明編纂實錄者已認為這幾句話與糾參主體無關。因此,據我的臆測,趙申喬之所以糾參戴名世,是因與他的長子即戴名世同科狀元趙熊詔有關。當時大氣候很不好,既有皇子結黨事件,又有南北闈的科場案,而北闈又與趙申喬有關,所以趙申喬不僅急於洗刷自己,而且要立新功,而如戴名世的“狂悖”言論文字為他人舉發,可能會牽連兒子掛上結黨之嫌,更有可能牽齣前科掄纔不當的另一科場案,所以不如先發製人,糾參戴名世,摘清乾係;但又不願得罪仕林,於是就在疏文中寫下這欲蓋彌彰的一筆。當然這隻是我的一種推理,尚無確證。
戴名世時年五十九,兩年前剛以會元摘取殿試榜眼,而參劾他的趙申喬為該科狀元趙熊詔之父,趙熊詔和戴名世一樣,科場潦倒多年,中狀元時也已四十六歲瞭,他會試時隻名列第二十七,殿試一舉奪魁,也算是齣人意料。
戴、趙兩傢本有同年之誼,又像趙申喬所說“臣與名世,素無嫌怨”,又為何要置對方於死地?近見來新夏教授“推理”,可能和南北闈科場案有關,北闈案牽涉到趙申喬,他怕戴名世的“狂悖”之語纍及狀元兒子,又急於洗刷自己立新功,也就先發製人瞭。但這也隻是“推理”而已。
戴名世年譜,道光年間有過無名氏所著一部行世,近年王樹民也有《重訂戴南山年譜》,但像此次戴廷傑《戴名世年譜》這樣“內容詳盡,資料豐富”,還屬先例。年譜“不僅校訂瞭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戴氏生平與傢族譜係資料,收錄瞭《戴名世集》未收之百餘篇佚詩文,而且在詳加考訂的基礎上,編有與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獄相關的六百餘人的生平傳記” (柴劍虹先生語) ,使“戴名世二百年前之沉冤藉此令世人詳其始末,明其究竟” (來新夏先生語)。
撰者以十年辛勞,潛心研究清代文字獄中一個重要人物戴名世,當其開始著筆著述時,必然會反復考慮運用何種編纂體裁與體例。以年譜體論定人物究竟是否閤適?我在以往曾對年譜這一史體有過一些研究,在所著《中國的年譜與傢譜》中曾說過:“年譜是史籍中的一種人物傳記……它是以譜主為中心,以年月為經緯,比較全麵細緻地敘述譜主一生事跡的一種傳記體裁。它雜揉瞭記傳與編年二體……”看來年譜比傳記更易於容納史料,理清脈絡,尤便於寓論斷於敘事。我在研究林則徐事功多年後,就寫瞭一部《林則徐年譜》,深感寫年譜比傳記更順手,更容易求真存實,更易於減少個人情感成分。而撰者這部年譜可謂把年譜的功能運用得非常自如,令人贊佩!
本書近百萬字,以漢語文言寫成,而作者戴廷傑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法國人,現為法蘭西學院漢學所研究員,是法蘭西學院華裔院士程抱一先生的高足,又師從過魏丕信和桀溺(Jean-Pierre Diény)兩位漢學大師。這個中文名,是二十五歲初遊遠東時,一個中國友人替他取的,這時還不知道“中國有桐邑,餘友未聞桐城有戴族”。後來他習漢語,博士論文研究戴名世,隻是巧閤。1986年,戴廷傑讀到王樹民編的《戴名世集》(中華書局,1986)曾去信感謝。那時他正做博士論文,已用瞭四年的時間“研究戴名世的一切”。現在戴廷傑又以十年之功完成這樣一部“極富古典文獻價值”的《戴名世年譜》,不說意義,單單他的古文功底,就要讓中國學者“赧然”瞭。
十年之間,戴廷傑幾乎每年都有中國之遊,尋訪輯佚,“不僅校訂瞭迄今為止最齊備的戴氏與傢族譜係資料,《戴名世集》未收之佚文,而且在詳加考訂的基礎上,撰有與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獄相關的六百餘人的生平傳記”,像來新夏教授所說,本書“無論資料的挖掘,史事的論述,牽涉的事實與人物,還是編纂體製等方麵”,都幾近全備。
這部專著最顯著的特色,是無論資料的挖掘,史事的論述,牽涉的事實與人物,還是編纂體製等方麵,都力求全備。所用的資料,除譜主本身文獻外,還有許多有關人物的著述。他徵引官書及一般常見書,也擴及方誌、雜書,在記事綱目下盡量附入詳盡的史料,並多加考訂。他對史事的敘述很細緻,如記譜主應試過程,從入場、考題、作文、薦捲到錄取、放榜、任職諸環節都有具體內容,不僅便於瞭解譜主參加科試的全過程,也映現瞭科舉製度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又如寫譜主的得罪,從被糾參入獄,株連親友,到懲處結案各個細節,都有滴水不漏的描述。撰者並不是孤立地記述譜主的生平,而是拓寬視野,將譜主置於整個政治、社會背景下,而與有關事務密切聯係來解析。對於株連所及的各方人物,都不是略加點錄,而是盡可能著其生平,使這部年譜不僅講清譜主的社會關係,而且也為研究那一時代學林活動提供大量的參考資料。
《戴名世年譜》的另一特色是頗有創意。撰者除瞭編纂常規應有的12捲正譜外,又增設瞭若乾具有原創意義的體例。如立《後譜稿》,始康熙五十三年即譜主被誅之次年,下迄清末,曆時二百年有零,用以記譜主身後案件餘波以及遺作的編纂、題記、刊行等情事。為曆來年譜編纂的創舉。《後譜稿》後,有附錄八種,錄存正譜未錄的譜主佚作、雜類文獻和近世題跋、近世雜記。並收錄譜主的舊譜、傳誌。另有文目編年、佚文代文文目等。涉及方麵之廣,幾乎將有關譜主資料,網羅殆盡,極便於研究參考。其最具創意者則為書前之圖版,撰者一反年譜常規,譜前未置譜主圖像,或示譜主銜冤沉埋不得顯其圖像,而特置興此大獄的檢舉人趙申喬朝服像,同時又置延緻戴名世之趙吉士消閑像,二趙並舉,撰者之褒貶自見。撰者插入的書影中有十幅是文禍後譜主名號被剜改塗抹的證據,如譜主所著《孑遺錄》所署“桐城戴名世田有著”一行被塗抹;《依歸草》後印本捲十“戴田有集序”被肢解為“戈二月集序”;《秀野草堂詩集》後印本將有關戴名世的詩句剜去兩行半,開“剜天窗”之先例等等。撰者在編譜之餘還念及讀者的使用,在譜末附入綜閤索引,分人名、地名、書名、篇名、酬酢、文獻等六種,以為讀者檢讀渠道。這些創意,不僅對年譜的編纂體例有所增益,亦以見撰者之匠心獨具。
年譜以編年為序,匯集豐富資料,確能體現長編作用,但撰者所持觀點及見解,亦多於體例安排,史料抉擇上發抒微言大義。如果撰者能在豐富資料基礎上,綜閤譜主一生行跡,撰寫一篇萬把字的《戴名世傳論》,有所是非褒貶,給以史傢評論,置於譜首,則將使譜主由平麵化為立體,給讀者以譜主的完整形象。譜傳結閤似可作為年譜體裁的發展方嚮,姑以此與撰者商榷。本譜徵引繁富,於其《文獻索引》中可一覽而得,惟大緻限於清人,而時人有關著述則甚鮮,蓋以時人所論述,足以見當前於譜主研究之水平,將對繼起者頗有裨益。一孔之見,是否有當,尚待商量。
對於這部年譜,戴廷傑先生自己做過如下論述:“像使用文言文一樣,一種模仿的作用。因為我整日接觸的就是文士的彆集,肯定也是因為我幾乎與課題溶為一體瞭。文士所作墓誌及傳記經常贊揚死者的發憤讀書及潛心勤學,古人的這種精神,今人也應藉鑒。文獻的裒輯需要耐心和經驗。文稿的考據需要邏輯和嚴謹,甚或一個簡單的正確判斷力。比勘則需要注意力集中,而標點是一種遊戲。當然這種遊戲藏有許多陷阱,我不能保證沒有掉進去。任何學術著作都會有或多或少的錯誤。學術著作的好壞之分就在於錯誤的多少。我隻是希望拙著中的錯誤(我自己已經發現瞭!)是在容忍度之內。您看,恐怕您過高估計瞭我的能力。如果說拙著有與眾不同之處,除瞭它齣自一個外國人之手,大概還是它的篇幅,即您所提到的九十萬字。在中國,年譜齣得很多,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譜都加上“長編”二字,是想錶明比一般年譜長。我沒有這樣做。我認為年譜即是年譜,沒有長短之分。拙著《戴名世年譜》本應與普通所見年譜的篇幅無甚兩樣,可是隨著新資料的發現,特彆是發現瞭戴名世六十篇佚文後,篇幅變得愈來愈大,最後超過瞭一韆頁。過去,年譜不求全麵,隻給齣要點,因此篇幅一般都不大,除非是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如王安石、硃熹等。今日,年譜是一種博學著作,如果能做到底,非常有益,起碼用處很大。我的運氣——運氣與纔能無關——是在研究上能夠走到底,或者說是走得比較遠。能做到這一點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在法國國傢科學研究中心工作有著很大的自由度。第二個原因是西方史學著作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研究也越深,篇幅也越大。我覺得由於體製的原因 (我們下麵還會談到) 和某些與中國近數十年的曆史有關的原因,中國在這方麵顯得有些落後。隨著中國的開放,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現在一批年輕的史學傢開始嶄露頭角,他們不像前輩那樣經曆瞭中國幾次大的起伏。在書齣版的幾個月前,得到瞭王樹民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深感遺憾。我本打算書一齣版,便贈獻給王老,現在他再也看不到我的研究成果瞭。我相信憑他以往的熱情和寬容,他一定會為《戴名世年譜》的齣版而欣慰。後來一想,這樣可能更好。王樹民先生經曆瞭新中國的誕生,可是以後的幾十年對研究舊中國國學的學者來說,並不能說是十分有利的年代;形勢雖然好轉,可是為時過晚,時間已流逝,人也步入晚年。戴名世生平未嘗不嘆息己命之不厚,己誌之不遂,認為是“未遇其時”。王老及其同代的學者真是在他們纔思橫溢的時期,沒有遇上有利的環境。現在情況完全改變瞭。中國傳統的史學隨著共和國的建立而消亡,新的史學正在建立,這將是形式和方法全新的現代史學。我投入這一課題的研究,剛好是處於兩個世界、兩代學者的轉接時期,這也是一種巧閤。晚十餘年,或二十年,我一定不需要寫《戴名世年譜》瞭,這一工作早會被中國學者完成!”
而對於譜後部分,他認為:“我不是第一個寫譜主死後情況的人。近些年齣的年譜中,有的已經這樣做瞭,雖然為數甚少。他們稱為《譜後》,即在“年譜之後”,加上類似一種附件。我更喜歡《後譜》,即“身後之譜”的意思。這樣更能體現某人死後通過留給後世的作品或記憶繼續存在。戴名世是一個文字獄的犧牲者,年譜應該試圖展現其作品如何逃過兩次焚毀重見光明,因此後譜的編撰就顯得極為重要。我最大的遺憾是來不及把後譜作得更深,所以隻能稱為《後譜稿》。是否有所創新,我不敢肯定,隻是盡力往深裏作。作年譜是一博學工作,博學工作隻有作深,纔會有真正的用途。比方說人名的考證。我所翻閱過的年譜,不說全部也是絕大部分,並不考證譜中所有人物的名字,甚或以字號為名。這樣不但不便於閱讀,而且與人物對不上號,與正名之道不閤。更關鍵的是忽略瞭某個文士的生平。搞曆史就應將人物的生活與環境、活動與來往,盡可能地串聯起來。對於戴名世來說,這些則顯得更為重要:他的交往錶現得越廣,越能體現《南山集》案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之大。因此我在人物考證方麵,下瞭較大的功夫,遺憾的是有些人名還是沒能考證齣來。作小傳也是本著這一精神,我盡可能去找信息較多的史料,比方說,查《清史稿》莫若查閱宗譜,查縣誌的粗泛列傳不如翻閱內容甚詳的墓誌。至於索引,是必不可少的。我力圖詳細以便查找。一本博學著作,非為讀而為用也。在我手中也不知過瞭多少本書,很多都是無法使用或是很少使用,因為沒有索引。我覺得在中國書中附索引的工作做得不夠。現代化的研究需要不斷地查閱大量的資料,索引的作用非常大。我撰寫年譜的這些努力,都是想到要方便讀者的使用。”
關於戴名世與桐城派,他有如下見解:“戴名世的文稿及其資料,我看瞭無數,我們就如同一對過從密切的老朋友,交往之深,時間之久,最後反而不知相互被對方什麼所吸引。戴名世的古文確實是悲憤慨慷,也正因此激怒瞭皇權。引發《南山集》案的,不僅是著名的 《與餘生書》,同時還有另外五篇(這批文章,譜中稱之為“緻禍六文”)。一百多年後,戴氏的悲憤慨慷也遭到瞭桐城三大傢方宗誠、戴鈞衡、蕭穆的反對,反對他“憤世疾俗”的態度。用現代讀者的眼光來看,戴名世的直言是一難得的優點:能夠高聲說齣眾人心中暗想的文士實在不多,因此更值得我們注意。我們也不能隻看到戴名世文章中激烈的措辭,我認為他的文體也十分清晰自然,正如他自己所提倡的“割愛”、“率其自然”、“平”與“質”。戴名世的句子經常寬舒流暢,較多地運用虛詞使得文章擴展明瞭,也很少使用偏字。(在一篇序中,他曾質問:奇字以為古乎?)記得曾與黃裳先生談及戴名世的文章,黃裳先生覺得戴名世的文章有些俗,他更欣賞方苞的文章。方苞的文章“凝縮而沉潛”,內容豐富,文字過硬。然而戴名世的文風錶麵看來樸素、不甚典雅,我認為這正是他的長處所在,起碼可稱為他的典型特徵,並足以證明他是一個重要的作傢,並非隻是文字獄的不幸受害者。至於他是否是桐城派的先祖,我從未真正提齣過這種問題,因為這一問題是我所研究的康熙時代以後纔提齣來的。眾所周知,姚鼐驚嘆“天下文章,其齣於桐城乎”之時,已是18世紀後期。姚鼐隻是提齣當時桐城作傢的影響,並不能算作為這一流派打下瞭根基,一個真正的流派乃是有著共同觀點的作傢匯聚在一起的有組織的團體。方宗誠在《桐城文錄》中指齣桐城派三個最重要作傢:方苞、劉大 、姚鼐,但同時又強調“三先生實各極其能,不相沿襲”。所謂桐城派實為一群無團體組織的作傢。如此看來,戴名世自然是屬於桐城派,並且是桐城派重要代錶作傢之一。在《桐城文錄》中,方宗誠選錄戴名世文稿的捲數僅次於方苞、劉大 、姚鼐,排列第四位,與方東樹並列。我認為有名文士方宗誠不會反對現今某些學者提齣的戴名世為桐城派鼻祖的說法。持這一觀點學者的依據之一,是戴名世和方苞的關係密切。拙著則會為此種觀點提供更多的證據,因為其中的史料反映齣二人的關係遠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密切。如果隻是從各學者所依據的文學理論而論,戴名世是否屬於桐城派是很難證明的。其實是無法證明的:怎麼可能證明一個作傢屬於他所生活的年代還不存在的一個流派呢?這並不是說提齣這種問題毫無意義,我隻是覺得從曆史學傢的眼光看,這幾乎是年代記述的誤差。最後我要補充一點:提齣這種問題,還是慎重為妙。近二三十年,有很多關於桐城派的文章,探討某作傢的文學思想,試圖找齣作傢間的相互關係或影響。我覺得許多文章缺少證據,隻是抽齣幾點或某些段落進行簡單地比較,並不重視原作和引文的上下文。所謂戴名世的文學思想,多半是根據戴名世為某些時文寫的序;像許多文士一樣,戴名世提倡“以古文為時文”,可是我們不要忘記戴名世在此類序中給齣的所謂寫作法則,實為一種極為特殊的文體練習,也即著名的八股文。戴名世在給侍郎趙士麟的信中要求趙氏撕毀他請人代寫而署戴氏的一篇序時,轉引《易經》中“君子以言有物”一句。難道也應將此作為戴名世文學思想的一部分嗎?難道便可與方苞的著名“義法”相比較,因為方苞曾提齣“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嗎?在這封信中,我怕看不齣彆的,隻看齣戴名世指責趙侍郎的妄貪虛榮。或許是我為收集史料,還原曆史真相已用盡力量,而無力登高俯視這些文學理論的問題。”
- 年譜
- 戴名世
- 年譜類
- 計劃中
- 特價書店
- 法國人
- 文字獄研究
- 工具書
本書為資料長編性質的清代著名文人戴名世的年譜。作者為法國法蘭西學院漢學所戴廷傑研究員,他曆十年之功,多次到中國各地數十傢圖書館及資料室以及譜主傢鄉調查、收集、抄錄、復製相關古籍,采用瞭以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為主的有關清宮漢、滿文檔案,不僅校訂瞭迄今為止最齊備的戴氏生平與戴氏及《南山集》文字獄相關的六百餘人的生平傳記,使此書成為極富古典文獻價值的研究清初期政治、文學、軍事的古籍整理類圖書。此書的八種附錄所收資料豐富、係統;六種索引則為使用者提供瞭便利。
具體描述
讀後感
去年有件事儿挺好玩的,早该给《上海书评》的读者报导一下。《书评》第178期(2012.3.11)刊出艾俊川《〈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一文后,立刻被布衣书局论坛转载。有网友转贴中华书局现任总经理徐俊的微博评论:“出差刚回,还没拜读这篇大作。数月前,《戴名世年谱》...
評分去年有件事儿挺好玩的,早该给《上海书评》的读者报导一下。《书评》第178期(2012.3.11)刊出艾俊川《〈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一文后,立刻被布衣书局论坛转载。有网友转贴中华书局现任总经理徐俊的微博评论:“出差刚回,还没拜读这篇大作。数月前,《戴名世年谱》...
評分去年有件事儿挺好玩的,早该给《上海书评》的读者报导一下。《书评》第178期(2012.3.11)刊出艾俊川《〈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一文后,立刻被布衣书局论坛转载。有网友转贴中华书局现任总经理徐俊的微博评论:“出差刚回,还没拜读这篇大作。数月前,《戴名世年谱》...
評分去年有件事儿挺好玩的,早该给《上海书评》的读者报导一下。《书评》第178期(2012.3.11)刊出艾俊川《〈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一文后,立刻被布衣书局论坛转载。有网友转贴中华书局现任总经理徐俊的微博评论:“出差刚回,还没拜读这篇大作。数月前,《戴名世年谱》...
評分去年有件事儿挺好玩的,早该给《上海书评》的读者报导一下。《书评》第178期(2012.3.11)刊出艾俊川《〈忧庵集〉是戴名世手稿吗?》一文后,立刻被布衣书局论坛转载。有网友转贴中华书局现任总经理徐俊的微博评论:“出差刚回,还没拜读这篇大作。数月前,《戴名世年谱》...
用戶評價
驚呆瞭 法國人用文言文寫的
评分驚呆瞭 法國人用文言文寫的
评分驚呆瞭 法國人用文言文寫的
评分驚呆瞭 法國人用文言文寫的
评分驚呆瞭 法國人用文言文寫的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圖書下載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