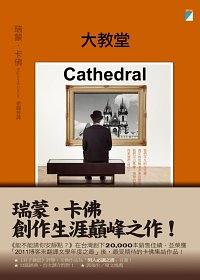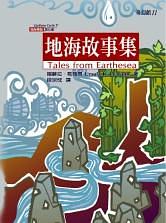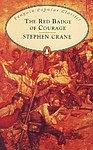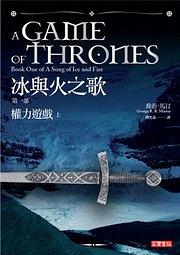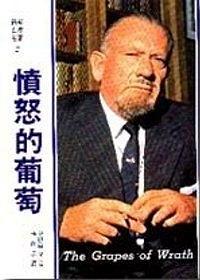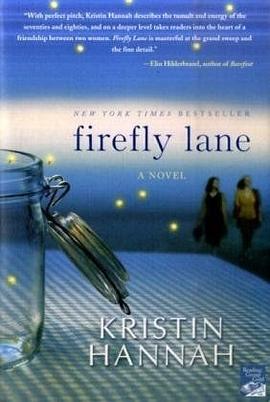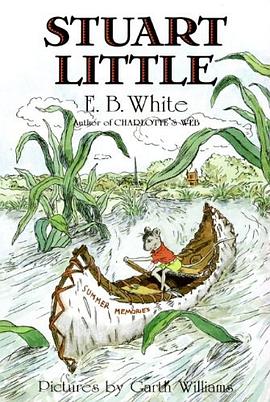前言
後現代的「死亡恐懼」新經典!
南方朔
十九及二十世紀之交的英國「跨世紀大詩人」湯瑪士.哈代(Thomas Hardy,一八四○─一九二八)寫過一首名詩〈兩者的交會─寫鐵達尼號的沉沒〉,已愈來愈重要的成了當今的時代意象。
哈代的這首詩為十一段三十三行,用詞嚴峻,將鐵達尼號和冰山這兩個主角參差對照;一個是人類繁華意志的巨大成就,它珠光寶氣、燦爛輝煌,是人類自信的代表,縱使朦朧如月的魚眼在看了後也嘆為觀止,體會得到它的自滿自傲;而就在同時,一個來自遠方的冰山也無聲無息的漂流靠近,為不祥的交會做著準備。這是一種不可能變成的可能。這首詩的後四段如此寫道:
而當這華麗的船體
其外形 優雅的氣度與色調更加清晰
這時陰暗遠方的冰山也愈大愈近。
它們顯得相當怪異
但沒有任何人的眼睛能看出
它們稍後歷史的緊密糾結在一起。
或它們那相呼應的走向
將相遇的徵象
在八月這兩個孿生子的命運。
直到歲月的編織工人
如此喊出「就是現在」 而人們都聽見
於是事情發生 兩個半球的撞擊聲響起。
哈代寫鐵達尼號的沉沒,他強調的是鐵達尼號所代表的人間世界,以及冰山所代表的自然世界,這兩個世界分屬不同的兩半球體,但人間世界的自大自滿及視而不見,卻使得這兩個半球體的不可能相遇反而變成了不可避免。也正因此,當代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近著《液態的恐懼》(Lignid Fear)裡,在談到當代的危機、風險及恐懼時,還特地將鐵達尼號及冰山這兩個意象借用,稱為「鐵達尼症候群」、「恐怖主義冰山」、「宗教基本教義派冰山」等。在鮑曼的思想裡,鐵達尼號和冰山的相遇,已成一個代表由不可能轉變為不可預測的恐懼與凶險。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被背叛的遺囑》(Les Testaments trahis)裡也指出:人的生命情境「有如被包裹在濃霧裡」,濃霧不是完全的黑暗,因此人仍能掌握咫尺的安全距離,但對安全距離外奔馳而來的文明力量則是純粹無能為力、無法預測,也完全束手無策的恐懼感。而恐懼已成了眼前世界,人類存在狀態的背景音樂!
其實,自從一九八○年代起,由於物質生產力量的加大,全球連鎖效應的擴大,文明的破壞力量已愈來愈接近新的臨界點。這也就是說,如果把整體的文明視為一隻駱駝,那麼人類所加諸駱駝的稻草重量,已開始大到這隻駱駝已露出疲態甚至病徵的時候。這也是一九八○年代後,人類的思想裡,對文明基礎的「現代性」的反思日增。到了一九九○年代,比較集大成的「全球風險理論」開始由德國思想家烏尚利希.貝克(Wlrich Beck)首創下成為新顯學之一的原因。所謂的「風險」,指的是在人為條件下,無論各種活動的過程、對自然的破壞,以及各種連動及反饋,已將人類無論個人、群體或全球,置於一種不可預測、凶險增高,易蒙傷害性等皆快速累積並擴大的新情勢之下;也正因為風險擴大,而且涉及的多半是人類社會的許多根本前提。「全球風險理論」在它的最基點上,遂以「反身現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為核心,試圖為人類走向找到另類起點。
而上述反省,乃是體制性與系統性的思維;若將風險、危機,以及因此而造成的習慣,落實到個人感性認知的層面,它所涉及的可能就是恐懼現象學,包括恐懼這個課題裡的死亡的恐懼這個最終極的退縮點了。
誠如齊格蒙特.鮑曼所指出的,當今人類所處的社會乃是有如液態流動的社會;古典的牧歌社會以及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充滿樂觀想像的合理現代社會,都早已一去不再返。而人們所面對的也就成了有如液態般流動並使人淹沒的恐懼。現在的恐懼不是可以估測度量其可能性的恐懼,而是早已跨過了臨界點,成了法國思想家路西安.費布里(Lucien Febvre)所謂「恐懼的時代」。它無所不在,人們被迫活在氣候異變的風雪洪水及乾旱火災,不知何時到來的地震海嘯,不可估量的病毒變種及狂牛病,以及不安全的食物、工業廢棄及毒物、被污染的水與空氣,恐怖活動造成的附帶傷害,暴力分子不知何地何時射出的槍彈……等之下。恐懼不是只發生在公共空間,甚至家裡的角落縫隙都可能爆出危險而使人恐懼。而所有的恐懼裡,最終極的即是演變為生命不可測也難預期的死亡恐懼。由於死亡即是「不存在」,因此它是人類探索本體意義裡最深的恐懼。儘管每天二十四小時裡不可能全都用來恐懼,但因恐懼是人本體的核心環節,這種本質性的恐懼縈繞難去,如何克服恐懼,特別是對死亡的恐懼,遂成了人類最大的焦慮源頭。
那麼,人們到底如何去面對死亡的恐懼呢?人們是否應像湯瑪士.馬希森(Thomas Mathiesen)所說的,將死亡恐懼的噪音使它無聲化,視而不見,使死亡恐懼取得正當性而成為一種常態?或者像古代食人族戰士一樣,藉著吃掉敵人而使自己強大俾克服恐懼?或者就是為了克服死亡的恐懼,刻意用一種嘻笑怒罵或將其消費掉的方式,將死亡這個問題成為一個「庸常化的問題」(Bancliby),從而能夠習慣並對死亡的恐懼開始麻木?這就像納粹一樣,將罪惡問題例行化和庸常化,遂使得罪惡在被稀釋後變得不再是罪惡,或者就是像古人一樣,去追尋古老的信仰,而後在信仰裡得以安頓?或者就是以一種認命而自我放棄的方式,將死亡美學化,視之為人生結束時最後的一場華麗?面對死亡的恐懼,人們不論真假,總是有很多選擇必須或不得不去做!
在替當前人類的恐懼,特別是對死亡的恐懼問題做了框架性的設定之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進入當代美國主要作家唐.德里羅的第八本,可能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白噪音》所呈現的世界了。
美國評論家隆納.蘇肯尼克(Ronald Sukenick)早已指出,從一九六○年代起,美國文學即由「後寫實」而進入了所謂的「後現代」這個新階段,過去那個全知的上帝作者業已死亡,於是一整代一整代的作者開始展開不同風格的演練與探索:有的意圖打破原有語義的牢籠,有的探索新的極簡風格,有的以後設方式用新的虛構來質疑歷史和現實的意義,有的則以諧仿來顛覆秩序。而在這個「後現代」風格演練裡,唐.德里羅無疑的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白噪音》也早已被確定成了當代經典之作。而他寫作《白噪音》時,年方四十九歲。
塞萬提斯在《唐吉訶德》裡曾曰:「恐懼有許多隻眼,可以看到地底下的東西。」而《白噪音》即是本討論當今死亡恐懼的著作。前面業已提到,當代思想在一九八○年代固然已開始碰觸意義的質疑,人的冷漠、中性及生態意識等課題,但有關風險、不確定、恐懼等尚未受到重視,而他在《白噪音》裡即已開始深入的碰觸到了這些課題。這等於證明了一個觀點,那就是傑出的小說家必然也是傑出的思想家的道理。《白噪音》裡的死亡恐懼的談法,有著全程式的、百科全書式的視野,縱使專業的思想工作者也少有人能達到它的這種層次,難怪此書出版後立即被人奉為怪異之作,並成為學院專題研究的題目了。
首先,《白噪音》乃是一部有相當難度的作品,特別是它的後設文本無論敘述方式、虛構情節如暗示及指涉效果都有很大的歧義性,預留了很大的想像解釋空間,當然也意謂著它有極大的誤淆空間。這時人們在理解這部著作時遂格外需要就它的思維模式裡著手。
本書取名《白噪音》,開宗明義即已指出了作者的關切對象。所謂「白噪音」,它的辭典意義是指一個空間裡,所有的動作所發表的各種音頻噪音之總合,包括了意圖壓制這些噪音的另外聲音在內。在本書裡,「白噪音」就等於是一切足以產生死亡恐懼以及人們意圖克服死亡恐懼的所有動作在內的聲音。易言之,本書就是在談論一個有關死亡恐懼的全程問題的議論式作品。
《白噪音》儘管情節單純,但它情節與議論緊密配合,還能帶動出有關死亡恐懼的全方位課題:
──它以美國中部小鎮「鐵匠鎮」和坐落於該鎮的「山上學院」為故事的發生地點。主角傑克.葛雷德尼乃是該學院「希特勒研究係」的系主任。他先後五次結婚,偕同現任妻子芭蓓和多次結婚所生的四個子女一起生活。小說開始時,乃是學校的開學之日,這些富裕之家的父母和子女返回學校小說以背景敘述的方式,將這些學生和他們的父母,以及葛雷德尼的家庭做了細密的敘述,將美國社會那種消費發達、瘋狂購物、媒體無聊當有趣、學術研究雞零狗碎、垃圾費物氾濫的景象暴露無遺。小說這樣的描寫,其實是以一種反諷的方式,將那種「提前消費,延遲付款」,現在消費著未來,一切都成了債務的後現代拜物文化做了最坦率的揭露。當一個社會的家庭團結儀式只是每週一次全家圍在一起看電視,包括消費著災難的畫面。這些景象其實正是在預告著災難的發生。本書的第一部,就像是鐵達尼號的起航,表面的光鮮亮麗、珠光寶氣的幸福燦爛下,其實流漾著對死亡的恐懼之背景哀歌。本書第一部裡,那些將記號視為真實,將幸福窄化為消費及製造讓人類心安的垃圾,將瑣碎的耽溺變成了學術的成功,將影像變成比真實更真實的「過現實」(Hyger-reality)的部分。其討論的廣度與深度,較諸一九八○年代後思想界對「後現代景像」的反思更不多讓。作家必須同時也是思想家的這個本質條件,在德里羅身上已得到了充分的論證,它那種有如蘭根式橫向應用的後現代敘述方式,每個重要的細節,在「恐懼死亡」的前題下,都可做出延伸的討論。
在第一部「波與輻射」之後,接著展開的第二部「毒氣事件」,已將風險及死亡威脅及恐懼,落實到一種叫做尼奧丁衍生物的巨毒化學物質的外洩事件,它將後現代消費社會賴以存在的「過分」行為,以有毒化學物質為焦點而展開。這個情節可謂已預告了印度的波帕肥料廠事件,人類的死亡恐懼裡,最核心的乃是對「脫文明化」、「脫法律與秩序化」的恐懼。
風險會造成人們的被驅離他們所在的「地點」,而進入另一種無政府的狀態。美國卡翠娜風災即是一例。而《白噪音》在這個部分,其實已等於將風險與死亡恐懼對公共秩序及行為的破壞做了最戲劇式的描述。混亂、無能也無力等脫序現象纛起,它是文明反噬的一齣災難劇,而小說主角葛雷德尼系主任即因在撤離逃難的過程裡下車加油,而暴露在有毒空氣中兩分半鐘。死亡恐懼開始因一個概念、一種可能性,正式的成了事件,進入了人的真實生命裡,鐵達尼號和冰山這兩個半球終於撞到了一起!
於是,我們就進入了本書的第三部,同時也是最百科全書,最可深入討論的「戴樂光景」了。被毒氣感染的系主任,開始正式面對死亡的問題,於是他努力的去追究妻子服藥的疑雲,最後發現妻子由於有死亡恐懼和焦慮,而透過應徵開始服用一種叫做「戴樂」的藥物,企圖克服死亡的恐懼和焦慮,為了能夠服藥,妻子甚至還聽命的犧牲肉體;而他的一個同事莫瑞.賈.西斯凱則向他灌輸類似食人族的觀念,在殺人裡使自己偉大並相信可因此得永生。於是教授遂向賣藥物的威利.明克報復。本書這部分的重要,不是在於它試圖想出任何解答,而是以一種百科全書的方式,藉著細節的展開,而去碰觸到「死亡恐懼」背後更深層的問題,包括死亡恐懼與邪惡、死亡恐懼與原始信仰。他的妻子企圖以藥物消費的方式,用外在化的藥物來解除內在的死亡恐懼,證明是場庸俗的情色荒誕劇;他的同事唆使他去殺人,以及他用希特勒的著作去抵擋以為的死神,這都是一種食人族的祕思,只有食人族可能讓自己強大到可以克服死亡威脅;而書中最後出現的德國瑪麗修女,則代表了古典的克服死亡恐懼的信仰力量,面對死亡威脅,我們不知道那真正的解答是什麼,只知道死亡威脅就像是毒氣事件後愈來愈華麗的日落景象,難道華麗的死亡,有如宇宙大爆炸一般,它就是人類的死亡與新生?我們沒有答案,但由主角幼子懷爾德誤撞車陣的驚險,似乎等於在告訴我們,死亡在這個後現代後工業的時刻,它就是如此的與人貼切,它是人類介意的鄰居和夢魘,它與我們共生。就像鐵達尼號與冰山已撞到了一起,我們要準備救人救己的舟楫!
《白噪音》這部著作卷帙浩大,在荒誕喧鬧的場景裡有著嚴峻的嘲諷與關心:它的確像《唐吉訶德》裡所說的,「恐懼有許多隻眼,可以看到地底下的東西。」德里羅在本書裡,的確用了他那多隻眼睛,把人類心靈底處的許多面向做了梳理,使得本書儼然成了一部新的死亡之書,它像地底下的那些已死者,用那喃喃的語調,在對活著的眾生做著有點模糊的叮嚀,我們聽不清楚在叮嚀什麼,但可以感覺到它就像是本文開始所引哈代那首詩一樣,海中魚群看著自大自滿的鐵達尼號滑過海面,它們在驚異中充滿了不祥的預感!
白噪音訪談
《白噪音》的創作動機來自於電視,原先想以Panasonic為書名……
Q:我們是否可以說,旅居海外的經歷成就了你的重要作品《白噪音》?
A:《白噪音》是我結束了海外居住,回國後創作的作品。那年是1982年,我開始注意到電視上有一些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事,那就是我們每天都在面對有害的東西。電視上的新聞訊息、氣象……全都像有害的東西,每天每刻在向我們放送。但這個現象少有人注意,除非是那些研究者或相關的人,否則不會有人提到這種有害物質對我們的傷害。而這個,就是我當初想寫《白噪音》的動機。
Q:這部小說,原先你並不是想用「白噪音」當書名,而想用Panasonic電器公司的商標名是嗎?
A:的確。Panasonic這個字其實可拆成兩字,前半的pan-是從希臘文來的,意思是「全部」;後半的sonic是來自拉丁文,意思是「聲音」。當初我認為這個字切中《白噪音》這部小說的意旨核心,非常適合。但後來並未獲得日本松下電器公司的同意,只好作罷。
Q︰這本書從書名的意涵便引起許多討論與研究,更讓人訝異的是,你在這麼嚴肅的主題下,很多對話卻寫得很喜感,描述也很幽默。你認為,「幽默」在你的小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你企圖從一些嚴肅、恐懼的主題中解脫的方法嗎?
A︰我不認為幽默一定是被用來對抗嚴肅或恐懼。它幾乎是這兩者的一部分。我們在遇到某些不舒服或恐懼的時刻,很可能會自發性地用幽默來化解,但事實上,在不舒服或恐懼產生的最初時刻,這種反射動作早已經隱然而生,以至於和它們合而為一。
Q︰你的作品中似乎有某種偏好,像在《白噪音》中,你會著墨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態,甚至把超級市場描述為一方聖地……
A︰我認為這是對日常生活和平凡時刻的重要感知。尤其在《白噪音》裡,我試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種光芒。有時這種光芒幾乎是可怕的,有時它又很可能帶著神性或是令人敬畏的質性。但,這種質性是真的存在嗎?呃,應該是吧。你知道,我不像小說裡的莫瑞那樣相信超級市場是個西藏的喇嘛廟,不過那個地方確實有些我們容易錯過的東西。
Q:可以針對莫瑞的這種心態再多說一些嗎?
A︰呣,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有個來自第三世界而從未離開家鄉的人,突然間被送到哪個城市的大型購物商場,他不會覺得興奮或恐懼嗎?他難道不會在一片光鮮亮眼的景致中,感覺到某種超過他生活經驗的東西即將發生?我覺得這種元素是存在於我的作品中,那是一種漂浮在我們觸覺和視覺邊界的奇觀。
Q:為何你的作品反覆提及希特勒和大屠殺?就拿《白噪音》來說,大學教授傑克就是透過在「希特勒研究學系」的工作來抑制自己對死亡的極端恐懼。
A:對傑克而言,他其實是找到了一種邪惡的保護模式。希特勒導致的破壞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傑克覺得藉此能讓自己隱身其中,而自己微不足道的恐懼會被這種巨大,被希特勒的怪異摧毀能力所吞沒。他覺得希特勒比生命還大---正如我們評論很多名人會說的---他甚至認為希特勒比死亡更大。像我們會去逃避恐懼感,是因為我們是如此深切地感受著它,在這裡其實一直有種強烈的衝突存在,我只是借傑克來突顯這種衝突。
我想這是一種我們都有的感覺,一種我們幾乎不願談論卻一觸即發的感覺。在《白噪音》中,我試圖將它與其他我們觸手可及卻不存在於經驗裡的感覺聯繫起來。這種非比尋常的恐懼,一直與我們試圖壓抑或逃避的死亡恐懼都是相關的。
·收起全部<<
精彩书摘
第一部:波與輻射旅行車群在正午時分抵達,在校園西區綿延成一條亮閃閃的長龍。它們魚貫向前,緩緩繞過那座橘色的工字鋼架雕塑,向學生宿舍前進。這些旅行車的車頂上載著仔細捆綁好塞滿或薄或厚衣物的旅行箱;載著裝有毯子、靴子皮鞋、文具書籍、床單枕頭和棉被的紙箱;載著捲起來的地毯和睡袋;載著腳踏車、滑雪屐、帆布背包、橡皮艇、英國式或西部式馬鞍。當車輛慢慢停下靜止後,學生們便蹦出車外,奔向後車門,一件件搬出裝在車廂裡的東西:立體音響、收音機、個人電腦;小冰箱和小瓦斯爐;裝在箱子裡的唱片和錄音帶;吹風機和電熨斗;網球拍、足球、曲棍球和長柄曲棍球桿、弓和箭;各式管制物品、避孕藥丸和避孕裝置;仍裝在購物袋裡的垃圾食物--蒜味洋蔥洋芋片、烤乾酪辣味玉米片、奶油花生小餡餅、「瓦飛洛」或「卡布斯」早餐麥片、水果軟糖和太妃爆米花、「咚咚啪」棒棒糖和「神祕」薄荷糖。
這二十一年來,每到九月份,我便會目睹這樣的景象上演。這是個輝煌的時刻,卻也一成不變。學生們以滑稽的叫喊或突然跌倒的動作向彼此打招呼,也總是一樣,互相吹噓這個夏天過得是如何精彩痛快。他們的父母待在汽車旁,頭暈眼花地站在大太陽底下,從各方面看見自己當年年輕的形象。那認真曬黑的皮膚,那精心裝扮過的臉龐以及顰蹙彆扭的表情。他們體驗到一種新生的感覺,領悟到一種共識。這些已為人母的女人個個伶俐機敏,保持節食中的苗條身材,她們知道所有人的名字。她們的丈夫甘心撥出時間,儘管距離遙遠卻也不在乎;他們身為父親的任務大功告成,個個身上都流露著一種已投保了高額保險的感覺。像這樣的旅行車隊大集合,比起他們一年之中會做的任何事,比起正式的宗教儀式或律法慣例,更能讓這些父母知道他們是思想相似精神相連的一群人,是同一個種族,是同一國的人。
我離開辦公室,走下山丘到鎮上去。鎮上有些建有塔樓、門廊高達兩層樓的房舍,住在這兒的人們皆擁有古老楓樹的遮蔭。這裡有希臘復興式與哥德式的教堂,還有一間精神病患收容院。病院擁有一條細長的柱廊、綴有花飾的老虎窗,以及一個極為陡峭的斜屋頂,尖頂處的裝飾物是一顆鳳梨雕塑。我、芭蓓和我們以前結婚所生的小孩,就住在這條寧靜街道的尾端。這裡曾經是一座森林,處處都是深淵幽谷,如今我們的後院外面就有一條高速公路,就位在我們的下方。每到深夜,當我們躺上黃銅床時,飛馳而過的稀疏車流把我們的睡眠圍裹在一種遙遠而平穩的呢喃聲中,宛如亡魂在夢境的邊緣喃喃自語。
我是山上學院「希特勒研究學系」的主任。這個學系是我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創建的,那天是個寒冷、明亮,偶有幾陣東風吹來的日子。當我向校長提出建議,認為我們應該設立一個專門研究希特勒生平與事蹟的系所時,他一眼便看出了可行性。這件事馬上造成轟動,完全可說是成功之舉。這位校長後來成為尼克森、福特和卡特總統的顧問,直到他死在奧地利某個滑雪場的纜車上為止。
在第四街和榆樹路的十字路口,車輛在此左轉就能抵達超級市場。一位女警窩在一輛盒子般的警車裡在此地巡邏,尋找違規停車、超速駕駛和過期的檢驗貼紙。鎮裡的每根電線桿上都貼有自製的尋狗尋貓啟事,其中還有些是出自小孩子的手筆。
芭蓓是個身材高大壯碩的女人,腰圍和體重皆頗為可觀。她亂蓬蓬的頭髮是金黃色的,但顏色相當特殊,是那種在過去被稱為「骯髒金黃」的顏色。如果她是個嬌小的女人,那麼這頭秀髮就會顯得太可愛、太俏皮和做作。但身材為她頭上這堆亂蓬蓬的東西找到合理存在的理由。大塊頭女性向來不管這種瑣事,她們缺乏在自己身體上耍伎倆的狡詐本領。
「妳應該過來看看的。」我對她說。
「過去哪?」
「今天是旅行車隊抵達的日子。」
「我又錯過了嗎?你應該早點提醒我才對。」
「它們一路延伸,經過音樂圖書館,排到州際公路上去了。藍的、綠的、紅的、棕的,那些旅行車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好像一支沙漠商隊。」
「你知道我這個人是需要提醒的,傑克。」
芭蓓不修邊幅,她具有一種粗心的尊貴特質,就像那些專注於某個嚴肅問題而忘了或疏於注意自己外表看起來是什麼模樣的女人。不過,這並非說她屬於那種被一般人認為注定要幹大事業的天才。她照料撫養小孩,在成人教育學程中教授一堂科目,還參加了一支為盲人朗讀的志工團體。每隔一星期她就會到鎮上邊緣,到那裡為一位名叫崔德威的老人朗讀。大家都叫他「崔老頭」,好像他是一個地標,一段岩層或一片陰鬱的沼澤。她唸給他聽的東西包括《全國詢問報》、《全國審查報》、《全國快報》、《環球》、《世界》和《星球》等雜誌。
既然這個老傢伙要求為這每周一次的活動增添點神祕成分,那又何必拒絕他呢?重點在於,不管芭蓓做什麼事,都會讓我感受到甜蜜的回報,覺得自己與一位充滿熱情的女人、一個白晝與充實生活的熱愛者,以及一種多元且濃厚的家庭氣氛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我看著她有條不紊地做這些事情,熟練中流露著自在與從容,一點也不像我之前的妻子們--她們都覺得自己與外界漸行漸遠。與情報工作打交道,使她們變成既自私又神經緊張的一群人。
「我想看的倒不是車隊。今年那群人看起來如何?有女人穿格子裙和針織毛線衣嗎?男人是不是穿騎馬夾克?騎馬夾克是什麼樣子?」
「有了錢,這些人都變得悠閒自在起來了。」我說:「他們真的相信他們有資格這麼做,而這樣的信念為他們帶來了健康。他們看起來都有那麼一點容光煥發。」
「有那種收入,我就會開始害怕死亡了。」她說。
「也許根本沒有我們所謂的死亡,只是一些文件會改變一下而已。」
「我們自己又不是沒有旅行車。」
「我們那輛車太小了,又是鐵灰色的,還有一扇車門整個鏽掉了。」
「懷爾德呢?」她突然驚慌失措叫起孩子的名字。她總是這樣,而她的這個小孩此時正動也不動地坐在後院的三輪車上。
芭蓓和我總是在廚房裡談天。廚房和臥室是我們的主要活動空間,是動力的所在,一切的根源。在這方面我和她很像,我們都把房子的其他地方當做貯藏室,用來堆放家具、玩具、過去的婚姻和各自的小孩所製造的未曾使用過的物品、過去的姻親留下的禮物、舊衣服和雜物,還有各式各樣的物件和箱盒。為什麼這些東西總是讓人感到悲哀呢?它們帶著一股黑氣、一種不祥的預感。不過它們讓我戒慎恐懼的倒不是個人的失敗和挫折,而是某個更普遍、無論規模或內容物都更大許多的東西。
芭蓓牽著懷爾德進來,讓他坐在廚房的流理台上。丹妮絲和史黛菲從樓上下來,我們談了一下她們在學校還需要什麼東西。沒多久,就到了午餐時間,我們進入一小段混亂和嘈雜的時刻。我們轉來轉去,拌嘴爭吵了幾句,把餐具弄得叮噹作響。我們從碗櫃、冰箱或彼此的盤子中攫取食物,直到大家都覺得夠了,才開始安靜地往我們色彩亮麗的食物上塗抹芥末或美乃滋。這時的氣氛是可想而知的嚴肅,是經過一番辛苦才獲得的報酬。餐桌上擺滿東西,芭蓓和丹妮絲用手肘互相頂了兩下,卻沒人開口說話。懷爾德還坐在流理台上,身邊是拆開的紙盒、捏皺的錫箔紙、亮閃閃的洋芋片包裝袋、幾盆包著保鮮膜的糊狀食物、易開罐拉環和束口繩、幾塊單片包裝的柳橙起司。亨利奇走進廚房,很仔細地觀察了眼前的場景,然後從後門溜走不見了。他是我唯一的兒子。
「其實我午餐並不打算吃這些東西,」芭蓓說:「我真的認真考慮過優格和小麥胚芽。」
「這句話好像在哪聽過?」丹妮絲說。
「好像就是在這裡吧。」史黛菲說。
「她總是買這些東西回來。」
「但她從來不吃。」史黛菲說。
「因為她認為,只要她不停買回來,總會為了解決這些東西而把它們吃掉。這好像是自己在欺騙自己。」
「這些東西堆滿半個廚房了。」
「結果她還是沒吃,把它們全扔了,因為已經過期壞掉了。」丹妮絲說:「然後,她只好重頭再來一遍。」
「不管妳往哪看,」史黛菲說:「看到的都是這些東西。」
「如果她沒有買這些東西的話,她會有罪惡感;如果她買回來卻沒有吃掉,她也會有罪惡感;看著這些東西堆在冰箱,她有罪惡感;把這些東西丟掉,她還是會有罪惡感。」
「這就像她本來想戒菸,卻又開始抽了。」史黛菲說。
丹妮絲十一歲,是個脾氣倔強的孩子。她幾乎每天都會帶頭,抗議母親一些浪費或有危險性的習慣。我是站在芭蓓這邊的。我告訴她,我才是需要拿出自制力來節食的人。我也不斷提醒她,我是多麼喜歡她現在的樣子。我還說,大塊頭的人內在多半是良善的,人們對大塊頭的人很容易產生信賴感。
但她還是對自己的臀部和腰圍感到不滿意,於是便去街上快走,去跑新古典中學體育場的台階。她說我是從她的缺點中找優點,因為這是我的本性,為保護愛人而欺瞞真相。在真相裡頭總是藏有一些東西的,她說。
樓上的煙霧警報器突然響起。要不是電池剛好沒電,就是這棟房子已經失火了。不過我們還是默默坐著把午餐吃完。
山上大學各系的主任都穿起了學士袍,不是那種長到拖地的華麗玩意,而是沒袖子只在肩部打皺褶的短外袍。我喜歡這種設計。我喜歡把手臂從袍子的皺摺處伸出來,用誇張的動作來看手錶。本來是很簡單的查看時間行為,但有了這個姿勢便不同了,漂亮的手勢能替生命增添不少浪漫色彩。那些在校園閒逛的學生,當他們看見系主任從旁走過,把手臂一舉從那身中世紀的外袍露出來,手上那支電子錶在夏末的薄暮中閃閃發光時,或許會把時間本身視為一種複雜的裝飾,一種出自人類意識的浪漫。當然,這身外袍是全黑色,也因此才能與任何衣服相配。
希特勒學系沒有自己專屬的大樓,我們窩在那棟名為「世紀大樓」的暗色石磚建築裡,與大眾文化系共用校舍。這個系的正式名稱叫「美國環境系」,他們是一個奇怪的群體,教授講師幾乎清一色是來自紐約的外國流亡者,個個機警伶俐,像一群惡漢,瘋了似的迷戀電影和一些莫名其妙的瑣事。他們在此破解文化的自然語言,為他們在歐洲度過的童年時期中所感受到的一些樂趣創造出一種堂而皇之的研究方法,例如用亞里斯多德學說研究泡泡糖包裝紙和洗衣粉廣告詞。這個學系的主任叫阿封斯(與某種速食品牌同音)?史東潘納多,是個胸部寬闊、臉色兇惡的男人。他的興趣是收集二戰前的汽水瓶,並固定展示在壁櫥裡。他底下所有的老師都是男性,全都穿著皺巴巴的衣服,全都需要好好修剪頭髮,咳起嗽來也不懂得遮攔。當他們湊在一起時,看起來就像是一群卡車司機公會的幹部,集合起來準備去指認某個同事殘破不全的屍體,讓人有一種充滿苦難、疑慮和不懷好意的印象。
莫瑞?賈?西斯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例外。以前曾是體育記者的他,今天邀請我與他一起吃午飯,去的是校園的餐廳。在那兒,不知名的食物散發著熟悉的味道,在我體內升起一個模糊和陰暗的記憶。莫瑞剛到山上大學不久,他肩背微駝,戴著一付小小的圓眼鏡,嘴邊蓄著一把安曼派教徒式的鬍鬚。他是客座教授,教的是「當代偶像」課程,看來現在的他似乎被那些大眾文化系的同僚搞得一頭霧水。
「我懂音樂,懂電影,我甚至認為就算漫畫書也具有非凡意義。但這裡卻有些正教授除了麥片盒子上的說明外,幾乎什麼也不讀。」
「他們可是我們這兒的先鋒派人士。」
「我不是在抱怨。我喜歡這裡,完全愛上這個地方。我喜歡這小鎮的景致,可以讓我遠離城市和性愛方面的糾纏。燥熱,城市對我而言,就只有這個字眼可形容。當你一下電車,走出車站,迎面而來的就是一股熱流。那是空氣、車輛和人們放出來的熱氣,是食物和性愛的熱氣,是摩天大樓的熱氣,是從地鐵和隧道飄出來的熱氣。城裡的氣溫總是比別的地方高八度以上。熱氣從人行道升起,由污染的天空降下。公共汽車呼出熱氣,購物的人群和工作的人群呼出熱氣。整個公共建設都是架構在熱的基礎上,拚命使用熱能,也造出更多熱能。科學家老愛談論溫度過高會讓世界滅毀,這個現象早已在進行了,你隨便到一個大型或中型的城市就能感覺到。既悶熱又潮濕。」
「莫瑞,你住哪?」
「住在一棟出租公寓,那地方完全把我給迷倒了。那是一棟離精神病院不遠的舊豪宅,裡面有七、八名房客,除了我以外,我看他們或多或少都打算在那裡住一輩子。那裡有個像懷有什麼恐怖祕密的女人,有個總是一臉憂愁的男人。有一個男人從來不離開房間,還有一個女人總是在信箱前一站就是幾個小時,不知道在等待什麼不會到來的東西。那裡有一個不知道自己身世的男人,還有一個身世複雜的女人。那地方有股味道,就像我特別喜歡的那種電影,帶有一種人生的不幸氣味。」
「那你屬於哪一種人?」
「我是猶太人。不然還能是哪種人?」
莫瑞身上倒有件事頗值得一提,他從頭到腳穿的都是燈芯絨布料衣物。我有種感覺,也許打從他十一歲開始,在一片擁擠的鋼筋水泥建築物中,他便為了某個遙不可及又難以理解的理由,把這種質地堅硬的布料和高深奧祕的知識學問給緊緊連繫在一起了。
「來到這個名叫『鐵匠』的小鎮,我不由自主快樂起來。」他說:「我來此是為了躲避桃花。城市裡充滿桃花、充滿性感可愛的人們。我再也不讓女人隨意操弄我身體的那個部分了。我在底特律曾和一個女人有過一腿,她需要拿我的精液去打離婚官司。可笑的是,我愛死女人了。無論哪一天,我只要看見她們修長的美腿踩著輕快步伐,像一陣從河面上吹來的輕風在清晨的微光中飄過,我就會為之傾倒。第二個可笑的是,其實我真正渴望的不是女人的身體,而是她們的心靈。女人的心靈,精精巧巧被侷限起來,以單方向大量流動,宛如一個物理實驗。和一位穿著褲襪、雙腿交疊的聰明女性說話,是多麼讓人愉快啊!特別是那尼龍布料發出的小小摩擦聲,更能讓這種快樂提升好幾個層次。第三個說來可笑的事實是,越是複雜、神經質和難搞的女人,我越會被她吸引。我欣賞簡單的男人,但女人要越複雜越好。」
莫瑞的頭髮濃密,看起來相當厚重。他的眉毛也很粗,幾綹鬈髮垂掛在他頸部兩側。下巴上那撮硬挺挺、缺了嘴邊髭鬚相伴的小鬍子,很像是能自由選擇的裝飾品,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黏上去或摘下來。
「你計畫教授什麼課程?」
「這正是我想找你聊聊的原因,」他說:「你用希特勒在此造出了一番奇妙事業。你創辦它、扶持它,讓它成為你的私人禁臠。在咱們這一帶,不管哪個學院或大學的教授,沒有人敢提到希勒特的名字而不朝你這個方向點個頭。當然,這只是個比方,但毫無疑問你這裡就是中心,就是這門學問的根源。他現在是你的希特勒,葛雷德尼的希特勒,你一定深深為此感到滿足。這所學院是因為希特勒研究才會國際知名,這個學系夠獨特,也夠有成就感。你以這個人物為中心,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系統,一個擁有無數次結構和相關研究領域的結構,一個歷史中的歷史。這個成就讓人驚豔。這是大師之作,夠聰明,又漂亮地先發制人。這就是我現在想做的,用貓王艾維斯來做。」
幾天後,莫瑞向我打聽一處號稱全美最上相穀倉的觀光勝地,於是我便和他開了三十幾公里的車,去到「農耕鎮」一帶的鄉間。那裡都是草地和蘋果園,無數道白色的籬笆在起起伏伏的田野間綿延伸展。很快的,那個廣告看板就出現了--「全美最上相穀倉」。在我們抵達之前,一共看見五個像這樣的廣告看板,而大約有四十輛轎車和一輛觀光巴士和我們一樣把車停在臨時停車場上。我們沿著一條小徑前行,來到一處地勢稍高、特別闢來供人觀賞拍照的地點。所有人都帶了相機,有些人還有三腳架、望遠鏡頭或過濾鏡。有個男人坐在一旁的亭子裡販賣明信片和幻燈片,上頭的風景和田野風光正是在這個地點所拍攝的。我們站在附近的樹林裡,看著這些拍照的人。莫瑞一直沉默不語,偶爾才拿出一個小本子,匆匆寫下幾個註記。
「根本沒有人看見穀倉。」他終於開口了。
但後頭跟了一段長長的沉默。
「一旦你看到關於穀倉的廣告牌,就不可能看見穀倉了。」
他又跌回沉默裡。帶著相機的人們離開高地,很快又有另一批人補上。
「我們來這兒不是為了捕捉形象,而是來這裡鞏固這個形象。每張相片都強化了這個氛圍。傑克,你能感覺到嗎?一種無名能量的不斷積累。」
說完,又是一段更長的沉默。亭子裡的男人忙著販賣明信片和幻燈片。
「來這裡根本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投降,我們看到的只是別人看到的東西。過去已有成千上萬人來此,將來還會有人一直來這裡,我們默許自己成為一種集體感知的一部分,實際上這卻扭曲了我們的視野。就某種程度而言,這就像一種宗教經驗,所有觀光活動都一樣。」
另一段沉默接踵而來。
「他們是為了拍照而拍照。」他說。
接下來他好一陣子沒開口。我們聽著咔嚓不停的快門聲,聽著那窸窣作響的底片捲動聲。
「這座穀倉在被人拍成照片之前是什麼模樣呢?」他說:「它以前是什麼模樣?和其他穀倉有何不同?又有何相似?這個問題我們根本無法回答,因為我們都見到了那些廣告看板,見到忙著拍照的這群人。我們非但脫離不開這個氛圍,而且此時此地的我們,也變成了這種氛圍的一環。」
說完這些話,他似乎感到非常愉快。
· · · · · · (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