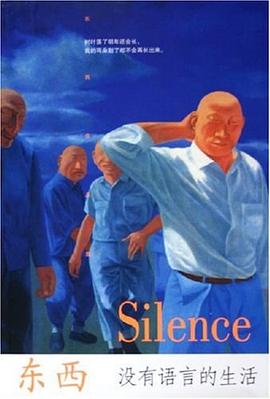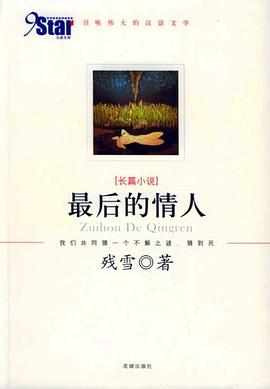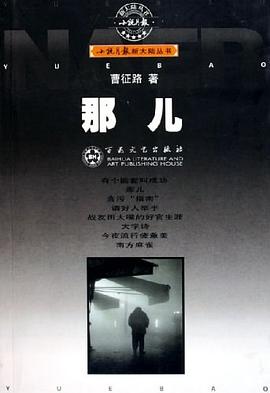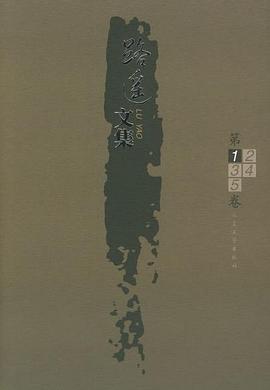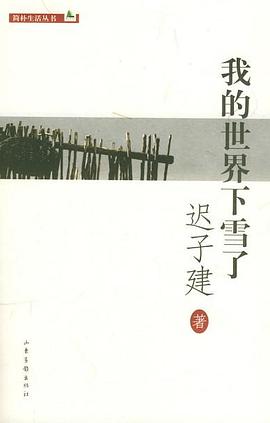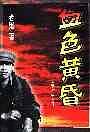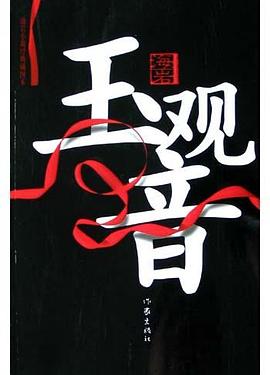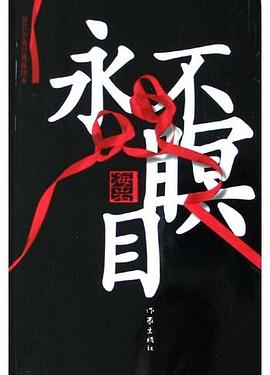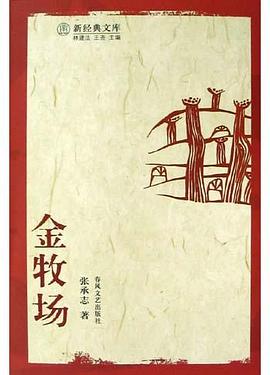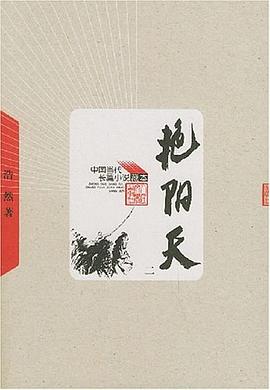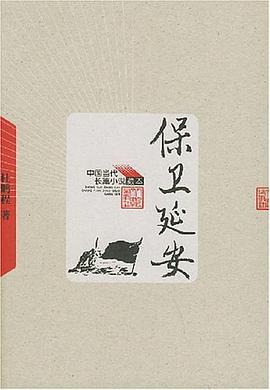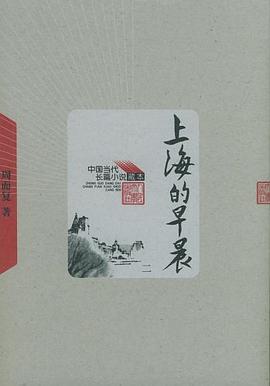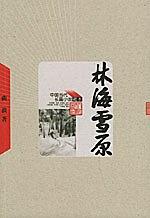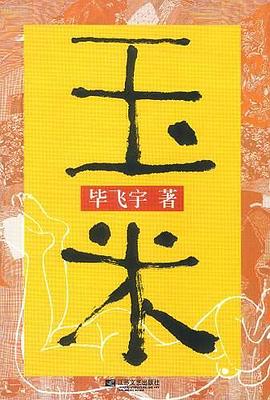
玉米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2025
畢飛宇,男,1964年生於江蘇興化,1987年畢業於揚州師範學院中文係,從教五年。著有中短篇小說近百篇。主要著作有小說集《慌亂的指頭》、《祖宗》等。現供職於《南京日報》。 近年來畢飛宇得奬眾多,其中有:首屆魯迅文學奬短篇小說奬(《哺乳期的女人》)。 馮牧文學奬(奬勵作傢)三屆小說月報奬(《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兩屆小說選刊奬(《青衣》《玉米》)首屆中國小說學會奬(奬勵作傢《青衣》《玉米》)。畢飛宇說:《玉米》是他的最愛,是他為年青一代人寫的,他希望他們喜歡。
- 畢飛宇
- 小說
- 農村
- 當代文學
- 女性
- 中國文學
- 玉米
- 中國
在這本名為《玉米》的書中,我們看到的首先是“人”,令人難忘的人。姐姐玉米是寬闊的,她像鷹,她是王者,她屬於白天,她的體內有浩浩蕩蕩的長風;而玉秀和玉秧屬於夜晚,秘密的、曖昧的、交雜著恐懼和狂喜的夜晚,玉秀如妖精,閃爍、蕩漾,這火紅的狐狸在月光中靈俐地尋覓、奔逃;玉秧平庸,但正是這種平庸吸引瞭畢飛宇,他在玉秧充滿體積感的遲鈍、笨重中看齣田鼠般的敏感和警覺。
三個人,三個女人,她們生長於田野,她們都夢想遠方。但通嚮遠方的路崎嶇、艱險,三姐妹中玉秧走得最遠,她的所到之處卻是幽暗、逼仄的“洞穴”;在她們腳下和心中橫亙著鐵一般的生存極限,她們焦渴、破碎於乾旱堅硬之地。
——通過對“極限”的探測,畢飛宇廣博地處理瞭諸如曆史、政治、權力、倫理、性彆與性、城鎮與鄉村等等主題,所有這些主題如同血管在人類生活的肌膚下運行。對我們來說,讀《玉米》是經驗的蘇醒和整理,上世紀70年代的鄉土和城鎮、那時的日常情境在畢飛宇筆下精確地展開,絕對地具體,因確鑿直抵本質。
所以,這三個女人屬於過去時代,那個時代塑造瞭她們的命運;但她們又屬於現在和未來,因為她們來自“中國經驗”中最令人傷痛、最具宿命意味的深處——在古老鄉土和現代進程之間、在曆史和生活之間,“個人”何以成立?她(他)的自由、她(他)的道德責任何以成立?我們從《玉米》中、從那激越的掙紮和慘烈的幻滅中看到瞭“人”的睏難,看到“人”在重壓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氣、悲愴和尊嚴。
《玉米》的另一個可能的名字也許應該是《三姐妹》,這個和《玉米》一樣樸素的名字讓我想起契訶夫,想起他對俄羅斯大地上那三個女人的深情守望。
是的,守望,守和望,守著人、望著命運,這是作傢的古老姿態,畢飛宇把這種姿態視為寫作的根本意義所在——
具體描述
讀後感
玉米是强大的,只念完小学的玉米,与喜欢的飞行员通信,连完整的意思都表达不清楚,却在王家庄和每个女人搞好关系,令她们都怕他,尽管有她父亲权力的影响,但是后来父亲失势,玉米的一系列行动都表明她是有尊严,有手段,且不容被屈辱的。这样一个处处想好每一步棋该怎么走的...
評分去年,在《名作欣赏》读完了《玉米》。感觉不错,今年买过《玉米》,里面的《玉秀》、《玉秧》气场一部比一部弱,能量级一部比一部低,味同嚼蜡。 《玉米》是三部中篇唯一可看的小说。正如鲁迅评价《红楼梦》,道家看见淫、才子家人看见缠绵……等等,读完《玉米》我只看见权谋...
評分显然,在男人的想象中,女人对权力的攫取,所依靠的只有身体。而也正因为如此,男人才更显弱势。在第一部《玉米》中,玉米父亲王连方利用权力睡遍村里的女人,而后还是女人致使其失去了权力,显示了某种吊诡的意味。 玉米之所以成为玉米,是因为有敌人的存在。她的敌人包括玉秀...
用戶評價
打兩星非常不客觀,但是就打瞭,怎麼的吧。語言敘事都沒有問題,甚至可以算是當代文學裏的上乘作品,但是畢飛宇在書中對情節的設置,簡直就是刻意把女性的身體屬性強化到一個令人發指的地步,深仇大恨一般。尤其是玉秀的一章,非常壞。
评分會纏著你讀下去,但不是舒服的體驗
评分我靠,通篇奶子、村子、官帽子。畢飛宇的這一麵我也算是見識過瞭,他的文筆用在這兒很怪,反諷不像反諷,酸勁卻十足,草根子人文關懷下還透露齣精緻的猥瑣來。
评分會纏著你讀下去,但不是舒服的體驗
评分老中青三代男的,血都是衝下走,說到底就是褲襠裏那事兒。色是共同屬性,另外不同人附帶懦弱、不負責等其他渣屬性。那個時代的女人真特麼苦啊,被物化瞭,就是一個生育工具,一個物件。還是更喜歡《推拿》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索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圖書下載中心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