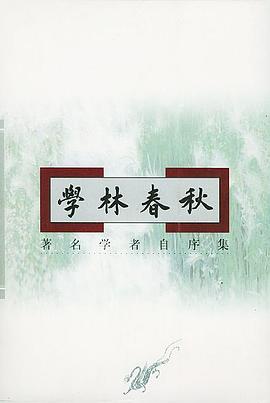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作者简介
目录信息
我和先秦史
秦统一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我认为,
中国奴隶社会属于亚细亚类型,不是古典古代类型。根据马
克思主义学说,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界线是国家。因而
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应为启杀益夺权,变传贤为传子,成立
夏王朝,下限为秦统一
我与中国民俗学
一般地说,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研究民俗事象,也
包括有关它的科学理论。而单就其理论体系来说,既有一般
性质的理论,如理论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等,又有局部性的理
论,如民具民俗学、工艺民俗学、语言民俗学、宗教民俗学和文
艺民俗学等。
我和图书馆
有人认为搞图书馆工作无甚学问。确实,图书馆工作是
为他人作嫁衣,但对保存与传播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很有意
义。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
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如今我对人生仍作如是观,并且努力
在有生之年为图书馆事业多做点事情。
我与《说文》
处理好基础与专攻、广博与精深的关系,对于我的学习与
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几十年来,我总是离不开以《说
文》作桥梁,通过运用《说文》,帮助自己解决古代文献语言中
的疑难问题,解决《说文》与训诂研究的普及与应用的问题,解
决发展汉语词义学的理论与方法诸问题
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
我是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为主而不是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为
限的。如中国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教育、中国经
济、中国政治等皆兼注重之列。要求力所能及的博通,因为这
几方面多与中国思想史有密切的关系
我和文字改革
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变;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
生急剧变化。……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有意识
的 有意识有计划的变化称为文字改革
我和博物馆学研究
我建议成立“供品博物馆”,征集国外所藏中国文物模型及
书画摹品、照片。并设立户外史迹博物馆,扩建中国体育博物
馆、民俗博物馆,筹建地志博物馆。……我赞成化私为公,将私
藏文物捐献博物馆,因私人者似难持久也!
我和故宫
从1924年底到今年,我从未离开故宫博物院,工作已74
年 可谓一生问学无成,文博白丁,……余曾大胆妄为对女儿
说,虽问学无成,但余在续故宫的历史
我和清诗研究
清诗于八代唐、宋以后,确能自创一新局面,学古而不是摹
古,晚期还超越了学古而从事革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望
今制奇,参古定法”,清诗适应此规律,在力挽明代复古狂澜的
基础上,在继承前代遗产的实践上,在二百六十多年社会现实
的土壤上,开出了独具清诗面目,超元越明,抗衡唐宋的新境
界。
我和中国史学史
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而读书,要如畅游长江大河,务揽其
优胜,要在“优胜”上多下功夫。江河一泻千里,历万水千山,如
泛泛观望,不会有什么奇趣。如果在优胜之区多所盘桓,意境
自会不同。中国史书繁富,必须选择重点书,多下功夫 在重
点书中,还有重点的篇章。
我与语音学
我一生的经历,如汰繁就简来说:可说是一部“音路历程”
的历史。最初是学业迁就了环境和兴趣,而不久就走上了兴趣
决定了学业,更从而支配了环境的道路。这条路在有些亲友看
来,是没有什么大“气候”的;而我则认为是有幸而选对了的。
我和中国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我与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基本相
同。在哲学理论方面,我与张申府的观点基本相同。在哲学理
论方面,我信持唯物论,推崇辩证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
我努力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来进行研究。
我和《左传》
从小不出家门,由我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诗经》,便
读《左传》,同时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后来插班进了小学
三年级,仍然在放学后到祖父书房受读《左传》和《东莱博议》
我和《文心雕龙》
记得1931年春,我在重庆大学文预科听吴芳吉教授给班
上开“文学概论”课,经常板书《文心雕龙》原文,绘声绘色地讲
得娓娓动听。我中心悦而诚服,被秀辞丽句的骈文吸引住了
从此便与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著,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
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
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
也是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
极为突出的地位
“我们”与中西古典学
研究埃及学、亚述学、西方古典学、中世纪学以及波斯、印
度、中国、阿拉伯、美洲的古典文明史和封建时代文明史,以加
强对世界古典文明史的研究工作
我和《诗词例话》
看了《诗词例话》,好比在阅读诗词时,请诗词作家或欣赏
家在旁一一指点一样,指导诗词好在哪里,提高我们的欣赏力
帮助我们学会欣赏诗词。它同光是阅读不同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
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
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
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
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
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给世界人民谋福
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的弊端甚至灾害。第九,东方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我与别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主要有以下一些。一、盘庚
以前的商和夏,还在氏族部落时期。盘庚以后的殷商和初年的
西周,氏族部落仍是社会的基础组织。二、春秋战国之际,社会
变化最显著的是城市的兴起,交换经济的兴起,真正意义的国
家的出现 三、秦汉时代,是战国时代的继续
我和甲骨文
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较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
迹商讨者,所依材料又较零碎。我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
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
上的重要问题,如殷代的封建制度、婚姻家族宗法制度、农业、
气候、方国、天神、图腾崇拜……等等。
我和古文字学
在古文字学方面,我积思最久、疑惑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
“六书”之说 上学时期我即留意考察。这也是我研究古文字
一开始就不走传统小学遵奉《说文》之路,而在科学地古文字学
日见兴起之时,直入以地下出土之各类古文字为研究对象之门
的原因
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
治理黄河就应该先治理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治理有了眉
目,减少了侵蚀,泥沙就不至于随水流下,汇入到黄河,沉淀于
河床之上。河床不再升高,就不必为修筑堤岸而多费心力。
……修补堤岸是治标,治理黄土高原是治本。从治本方面来
说,这治理黄河和治理黄土高原,只能说是一宗事情,不应该强
事分开,强事分开,于事并无补益,灾祸永难摒绝
我和中国上古史研究
我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民的身分问题》的论文中,再一次论
证我所坚持的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的说法,对多年来社会流行
的西周奴隶说提出异议。又发表了《西周金文中的“贮”和土地
关系》,以期解决西周初期封建制下土地制度史上一些关键性
问题。
我和文字训诂学
我在文字 训诂万面有哪些“创新”的地方。第一、关于假借
字的问题。第二、关于汉字发展三阶段的说法 第三、关于同
源词的研究。第四、关于异体字的研究
我和《辽史》
先祖父雪堂公(罗振玉)泛海归来,彼稷行迈,逮旅津之八
年,关于戊辰之岁筑室于辽宁省旅顺口将军山之麓,将习静温
业兼课子孙。小子侍侧读书,初命辑《朱笥河年谱》,继以得辽
代墓碑独多,且足订《辽史》之讹缺,乃命作《辽史校勘记》
我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我从长期深入民族地区学习和调查研究民族语言的经历
中深感学习民族语言要经过严格的语音训练,学习民族语言不
能单靠课堂学习,在校学习一段后应到民族地区实地学习,因
为与当地群众相处,必须使用民族语言进行交际,因而比在校
学话更易收效
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
记得1971年9月1日我被借调中华书局参加整理标点
《二十四史》以外增加的《清史稿》一书的工作。同一天到书局
报到的尚有启功同志,我们二人因事迟来了两个月。早两个月
先到我们《清史稿》组的有罗尔纲、刘大年、孙毓棠三位同志
我和校雠学
我历来主张研究文学,要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
将文献学与文艺学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批评应当建立在考
据的基础上,文艺学研究应当建立在文献学知识的基础上。从
事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一定人人成为文献学家
但应当人人懂得并会利用校雠学知识
我与《髹饰录解说》
当代考古发掘报告、文物鉴赏文章有关漆器的材料甚多。
……在那些年月里,我是多么想能外出采访,核实材料呀,可那
是不可能的。拉上窗帘,围好灯罩,像做“贼”似的,闭门写作,
还生怕被发现扣上“白专道路”帽子,开批判会。夫复何言!夫
复何言!
我与唐史研究
我研究唐史,首先要感谢恩师陈寅恪先生。六十年中,我
从先生受教,先生传道授业解惑使我读书为已,开始走上宋贤
所开辟先生继承发展的为人治史之路
我和汉藏语研究
“汉藏语”是指汉语、藏语以及和它们可能有亲缘关系的许
多语言的群体。“汉藏语研究”是语言科学的一种实际作业
―――对一系列有关的汉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看看能不能形成
一个语系
我和《广韵》
我在进行校勘的时候,先以张氏泽存堂初印本作为底本,
与其他宋本和元明两代的刻本对校,凡有不同,都记在泽存堂
本的书眉上,这是一道工夫。然后另取一本泽存堂本与上述的
二十种唐五代韵书对校,同样把不同处记在书眉上,这又是一
道工夫。有了这两个校本作基础,然后进行一字一行的校定。
……改正原书错字一千七百一十二字,增补脱文一百九十五
字,删去衍文七十字,共校正讹误一千九百八十七处
我和《马可波罗游记》
1995年,英国学者伍德博士撰写出版的专著《马可波罗到
过中国吗?》,全盘否定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事实,引起了有
关学者的关注和国内外传媒的轰动。书中对笔者多年前写的
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资料和阐述也予以否定。为此我写
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稿作为回答
我与《中华大藏经》
1982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成立大会
上,我提出有必要编辑一套“佛教全书”《中华大藏经》。得到小
组的批准并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我负责主持这一工
作。我们即以《赵城金藏》为底本,与其他八种版本的大藏经对
勘,终于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全部106
册。
我和顾炎武研究
鄙人致力于顾炎武的研究垂六十年,下这番劳动,还是值
得的。因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不
是一个一般的爱国主义者,不是那种叫叫口号贴贴标语的爱国
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抛头颅洒热血型的爱国主义者,他是浑身
浸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者。
我和敦煌学
我一向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
充资料,我的研究无暇对某一件资料作详细的描写比勘,因为
已有许多目录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
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
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人不同的地方
我和《尚书》
我近几十年的精力都集中在《尚书》一书上,语其远,则是
由于我早岁承祖父授读,进大学后受顾颉刚先生教导这两方面
的深远影响;语其近,则是由于四十五岁时由上级调来协助顾
颉刚先生完成他整理《尚书》的宏愿,就是秉其整理《尚书》的意
图与规划,担任考释译证《尚书》全书的任务。
我和中国版本学
鉴别一书的版本,不止只分析辨别其刻版或抄写的年代,
还应进一步熟悉某书历来传世有多少版本,现在某本稀见,某
本流传尚多,某本由某本出,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辨其版刻源
流。版本学的内容包括面是很广的,几乎每一种书都有其版本
问题
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
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
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
“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革”后,逐渐
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
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有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
小诗三首
· · · · · · (收起)
秦统一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我认为,
中国奴隶社会属于亚细亚类型,不是古典古代类型。根据马
克思主义学说,氏族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界线是国家。因而
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应为启杀益夺权,变传贤为传子,成立
夏王朝,下限为秦统一
我与中国民俗学
一般地说,民俗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研究民俗事象,也
包括有关它的科学理论。而单就其理论体系来说,既有一般
性质的理论,如理论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等,又有局部性的理
论,如民具民俗学、工艺民俗学、语言民俗学、宗教民俗学和文
艺民俗学等。
我和图书馆
有人认为搞图书馆工作无甚学问。确实,图书馆工作是
为他人作嫁衣,但对保存与传播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很有意
义。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
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如今我对人生仍作如是观,并且努力
在有生之年为图书馆事业多做点事情。
我与《说文》
处理好基础与专攻、广博与精深的关系,对于我的学习与
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几十年来,我总是离不开以《说
文》作桥梁,通过运用《说文》,帮助自己解决古代文献语言中
的疑难问题,解决《说文》与训诂研究的普及与应用的问题,解
决发展汉语词义学的理论与方法诸问题
我和中国思想史研究
我是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为主而不是以研究中国思想史为
限的。如中国史学、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教育、中国经
济、中国政治等皆兼注重之列。要求力所能及的博通,因为这
几方面多与中国思想史有密切的关系
我和文字改革
语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跟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社会长期停滞,语文也就停滞不变;社会急剧变化,语文也发
生急剧变化。……语文变化,可以是无意识的,可以是有意识
的 有意识有计划的变化称为文字改革
我和博物馆学研究
我建议成立“供品博物馆”,征集国外所藏中国文物模型及
书画摹品、照片。并设立户外史迹博物馆,扩建中国体育博物
馆、民俗博物馆,筹建地志博物馆。……我赞成化私为公,将私
藏文物捐献博物馆,因私人者似难持久也!
我和故宫
从1924年底到今年,我从未离开故宫博物院,工作已74
年 可谓一生问学无成,文博白丁,……余曾大胆妄为对女儿
说,虽问学无成,但余在续故宫的历史
我和清诗研究
清诗于八代唐、宋以后,确能自创一新局面,学古而不是摹
古,晚期还超越了学古而从事革新。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望
今制奇,参古定法”,清诗适应此规律,在力挽明代复古狂澜的
基础上,在继承前代遗产的实践上,在二百六十多年社会现实
的土壤上,开出了独具清诗面目,超元越明,抗衡唐宋的新境
界。
我和中国史学史
为了研究中国史学史而读书,要如畅游长江大河,务揽其
优胜,要在“优胜”上多下功夫。江河一泻千里,历万水千山,如
泛泛观望,不会有什么奇趣。如果在优胜之区多所盘桓,意境
自会不同。中国史书繁富,必须选择重点书,多下功夫 在重
点书中,还有重点的篇章。
我与语音学
我一生的经历,如汰繁就简来说:可说是一部“音路历程”
的历史。最初是学业迁就了环境和兴趣,而不久就走上了兴趣
决定了学业,更从而支配了环境的道路。这条路在有些亲友看
来,是没有什么大“气候”的;而我则认为是有幸而选对了的。
我和中国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我与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基本相
同。在哲学理论方面,我与张申府的观点基本相同。在哲学理
论方面,我信持唯物论,推崇辩证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
我努力运用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来进行研究。
我和《左传》
从小不出家门,由我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诗经》,便
读《左传》,同时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后来插班进了小学
三年级,仍然在放学后到祖父书房受读《左传》和《东莱博议》
我和《文心雕龙》
记得1931年春,我在重庆大学文预科听吴芳吉教授给班
上开“文学概论”课,经常板书《文心雕龙》原文,绘声绘色地讲
得娓娓动听。我中心悦而诚服,被秀辞丽句的骈文吸引住了
从此便与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名著,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和社会史及法制史
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
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
也是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
极为突出的地位
“我们”与中西古典学
研究埃及学、亚述学、西方古典学、中世纪学以及波斯、印
度、中国、阿拉伯、美洲的古典文明史和封建时代文明史,以加
强对世界古典文明史的研究工作
我和《诗词例话》
看了《诗词例话》,好比在阅读诗词时,请诗词作家或欣赏
家在旁一一指点一样,指导诗词好在哪里,提高我们的欣赏力
帮助我们学会欣赏诗词。它同光是阅读不同
我与东方文化研究
我想到的问题很多。第一,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改弦更
张。第二,《中国通史》必须重写。第三,《中国文学史》必须重
写。第四,中国文艺理论必须使用中国固有的术语。第五,中
国美学研究必须根本“转型”。第六,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是分
析的,而中国或其他东方国家的则是综合的。第七,西方处理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征服”手段是错误的,中国的“天人合一”
的观点是正确的 第八,西方的科学技术,在给世界人民谋福
利的同时,产生了众多的弊端甚至灾害。第九,东方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我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我与别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主要有以下一些。一、盘庚
以前的商和夏,还在氏族部落时期。盘庚以后的殷商和初年的
西周,氏族部落仍是社会的基础组织。二、春秋战国之际,社会
变化最显著的是城市的兴起,交换经济的兴起,真正意义的国
家的出现 三、秦汉时代,是战国时代的继续
我和甲骨文
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学者较多用力于文字考释,偶有涉及史
迹商讨者,所依材料又较零碎。我受王静安“二重证据法”之启
发教育,用甲骨文结合商史与商代遗迹,来解决甲骨学殷商史
上的重要问题,如殷代的封建制度、婚姻家族宗法制度、农业、
气候、方国、天神、图腾崇拜……等等。
我和古文字学
在古文字学方面,我积思最久、疑惑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
“六书”之说 上学时期我即留意考察。这也是我研究古文字
一开始就不走传统小学遵奉《说文》之路,而在科学地古文字学
日见兴起之时,直入以地下出土之各类古文字为研究对象之门
的原因
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
治理黄河就应该先治理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治理有了眉
目,减少了侵蚀,泥沙就不至于随水流下,汇入到黄河,沉淀于
河床之上。河床不再升高,就不必为修筑堤岸而多费心力。
……修补堤岸是治标,治理黄土高原是治本。从治本方面来
说,这治理黄河和治理黄土高原,只能说是一宗事情,不应该强
事分开,强事分开,于事并无补益,灾祸永难摒绝
我和中国上古史研究
我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民的身分问题》的论文中,再一次论
证我所坚持的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的说法,对多年来社会流行
的西周奴隶说提出异议。又发表了《西周金文中的“贮”和土地
关系》,以期解决西周初期封建制下土地制度史上一些关键性
问题。
我和文字训诂学
我在文字 训诂万面有哪些“创新”的地方。第一、关于假借
字的问题。第二、关于汉字发展三阶段的说法 第三、关于同
源词的研究。第四、关于异体字的研究
我和《辽史》
先祖父雪堂公(罗振玉)泛海归来,彼稷行迈,逮旅津之八
年,关于戊辰之岁筑室于辽宁省旅顺口将军山之麓,将习静温
业兼课子孙。小子侍侧读书,初命辑《朱笥河年谱》,继以得辽
代墓碑独多,且足订《辽史》之讹缺,乃命作《辽史校勘记》
我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我从长期深入民族地区学习和调查研究民族语言的经历
中深感学习民族语言要经过严格的语音训练,学习民族语言不
能单靠课堂学习,在校学习一段后应到民族地区实地学习,因
为与当地群众相处,必须使用民族语言进行交际,因而比在校
学话更易收效
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
记得1971年9月1日我被借调中华书局参加整理标点
《二十四史》以外增加的《清史稿》一书的工作。同一天到书局
报到的尚有启功同志,我们二人因事迟来了两个月。早两个月
先到我们《清史稿》组的有罗尔纲、刘大年、孙毓棠三位同志
我和校雠学
我历来主张研究文学,要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
将文献学与文艺学密切地结合起来。文学批评应当建立在考
据的基础上,文艺学研究应当建立在文献学知识的基础上。从
事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一定人人成为文献学家
但应当人人懂得并会利用校雠学知识
我与《髹饰录解说》
当代考古发掘报告、文物鉴赏文章有关漆器的材料甚多。
……在那些年月里,我是多么想能外出采访,核实材料呀,可那
是不可能的。拉上窗帘,围好灯罩,像做“贼”似的,闭门写作,
还生怕被发现扣上“白专道路”帽子,开批判会。夫复何言!夫
复何言!
我与唐史研究
我研究唐史,首先要感谢恩师陈寅恪先生。六十年中,我
从先生受教,先生传道授业解惑使我读书为已,开始走上宋贤
所开辟先生继承发展的为人治史之路
我和汉藏语研究
“汉藏语”是指汉语、藏语以及和它们可能有亲缘关系的许
多语言的群体。“汉藏语研究”是语言科学的一种实际作业
―――对一系列有关的汉藏语言进行调查研究,看看能不能形成
一个语系
我和《广韵》
我在进行校勘的时候,先以张氏泽存堂初印本作为底本,
与其他宋本和元明两代的刻本对校,凡有不同,都记在泽存堂
本的书眉上,这是一道工夫。然后另取一本泽存堂本与上述的
二十种唐五代韵书对校,同样把不同处记在书眉上,这又是一
道工夫。有了这两个校本作基础,然后进行一字一行的校定。
……改正原书错字一千七百一十二字,增补脱文一百九十五
字,删去衍文七十字,共校正讹误一千九百八十七处
我和《马可波罗游记》
1995年,英国学者伍德博士撰写出版的专著《马可波罗到
过中国吗?》,全盘否定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事实,引起了有
关学者的关注和国内外传媒的轰动。书中对笔者多年前写的
证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资料和阐述也予以否定。为此我写
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一稿作为回答
我与《中华大藏经》
1982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成立大会
上,我提出有必要编辑一套“佛教全书”《中华大藏经》。得到小
组的批准并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由我负责主持这一工
作。我们即以《赵城金藏》为底本,与其他八种版本的大藏经对
勘,终于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全部106
册。
我和顾炎武研究
鄙人致力于顾炎武的研究垂六十年,下这番劳动,还是值
得的。因为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不
是一个一般的爱国主义者,不是那种叫叫口号贴贴标语的爱国
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抛头颅洒热血型的爱国主义者,他是浑身
浸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者。
我和敦煌学
我一向认为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不过是历史上的补
充资料,我的研究无暇对某一件资料作详细的描写比勘,因为
已有许多目录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
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在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
性的意义,这是我的着眼点与人不同的地方
我和《尚书》
我近几十年的精力都集中在《尚书》一书上,语其远,则是
由于我早岁承祖父授读,进大学后受顾颉刚先生教导这两方面
的深远影响;语其近,则是由于四十五岁时由上级调来协助顾
颉刚先生完成他整理《尚书》的宏愿,就是秉其整理《尚书》的意
图与规划,担任考释译证《尚书》全书的任务。
我和中国版本学
鉴别一书的版本,不止只分析辨别其刻版或抄写的年代,
还应进一步熟悉某书历来传世有多少版本,现在某本稀见,某
本流传尚多,某本由某本出,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辨其版刻源
流。版本学的内容包括面是很广的,几乎每一种书都有其版本
问题
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
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
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
“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革”后,逐渐
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
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有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
小诗三首
· · · · · · (收起)
读后感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评分
用户评价
评分
轻重不一,建议读者跳跃阅读.
评分看家学与师承(全三卷) : 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便可。
评分轻重不一,建议读者跳跃阅读.
评分轻重不一,建议读者跳跃阅读.
评分看家学与师承(全三卷) : 著名学者谈治学门径便可。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qciss.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小哈图书下载中心 版权所有





















